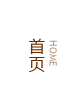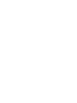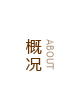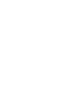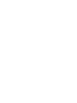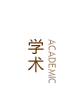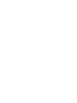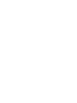庞薰琹艺术之路的启示
2010-03-17 01:23:00来源:庞薰琹美术馆点击:8977
活动时间:2010-3-17
活动地点:常熟市第一中学
主讲人:庞 均(庞薰琹之子、台湾艺术大学教授)
常熟美术馆根据录音整理

同学们好,我很羡慕你们,从我的视点来看,第一排到最后一排,你们每个人的脸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你们是那么的年轻、那么有活力。我想你们现在大多数应该在十四五岁之间,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年龄。相信你们都很喜欢艺术、喜欢美术,我更希望,在多年以后,在座的同学当中,有人会成为常熟的艺术家,全国有名的艺术家,甚至是世界有名的艺术家。我想,从现在开始,如果你们努力学习,逐渐进入学艺的状态,那么,这个理想是一定可以实现的。为什么?因为我想告诉你们,我是十三岁上大学,十八岁毕业,就是说我比你们现在还小的时候就进入到杭州国立艺专学习,后来变成杭州美术学院,那时像黄宾虹这些老前辈都还在世。之后我转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在我将要毕业的时候,徐悲鸿已经去世了,当时,齐白石是美术家协会的主席,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可以这么讲,当年我是全国最小的一位大学毕业生。现在我的同学已有不少去世了,活着的同学也都在八十五岁左右,或者年纪更大。我心情很不好,活着的同学越来越少了,但看到你们我就非常高兴。
到了常熟,大家多少知道庞薰琹这个名字,本来是让我用简单的方式来介绍一下,但是现在看来,《庞薰琹艺术之路的启示》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大了,用很短的时间不可能把它说得很清楚。在这里我想用一种讲故事的,比较活泼的方式来展开这个话题。希望你们听后,对自己的艺术乃至人生之路有所启示。
我父亲早已去世,如果他还在世的话,就是104岁的老人了。为什么要选《庞薰琹艺术之路的启示》这个话题呢?因为我希望通过对我父亲的著作、作品所反映艺术思想的解读,结合他的艺术之路,进一步了解、认识他的人生观,从而对我们后来的人会有所启示,尤其是常熟人。
在常熟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出现了很多有名的文人,最早的可谓孔子的弟子言子。言子在世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他四十多岁时就去世了。其实用孔子的说法,言子最像他自己,所以言子去世时孔子是非常伤心的。两千多年来,我们常熟出了很多名人,你们在座的是常熟文化发展的希望。
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介绍庞薰琹艺术之路,先看看照片吧,这就是他年轻的时候,还是在留法前后照的,大约二十多岁吧。最右边的那张比较老了,七十多岁吧,不过这个年龄可能比我现在还小一点。
我父亲是十九岁去的法国,去之前是在上海震旦医学院学习,他也是很小的年龄进大学。上海震旦学院是一个法国人办的学校,所以从一年级开始就要讲法文,我父亲从震旦学院毕业出来以后法文非常好,就到了法国。本来学医的他是应该到德国去留学,但是法国巴黎的艺术世界对他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他从小就喜欢艺术,所以后来就留在法国学习艺术了。
下面有一段简短文字的介绍,你们可以在我父亲的回忆录中看到。我取了最重要的一段话:“ 我始终走我自己的路,我的一生是探索探索再探索的一生。” 这句话,看似很平常,但却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有许多人生的故事。
前面我讲到他十九岁去巴黎,到了那以后,他非常激动,因为法国对他来讲是全新的概念,他不仅可以看到许多文艺复兴以来著名的油画原作,而且还能看到很多现代艺术设计。
我父亲在法国期间,起初是在巴黎大学学习音乐和美术,后来就想转到巴黎美术学院去。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巴黎美术学院已经开始没落了。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巴黎美术学院实际上是在学院派的没落阶段。像毕加索、马蒂斯这些人那时候已经非常有名了,就是说艺术已经由传统走向现代,但是巴黎美术学院的教育还是比较僵化的。我父亲想进巴黎美术学院去学习,被他最好的朋友常玉阻止了,他说:你现在还进巴黎美术学院?那里是学不到什么的。所以后来包括我父亲在内,他们就到艺术家的工作室游走、学习。
我们也知道,现在的社会大家都在追求一张文凭,好像从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然后读研拿个硕士学位,再继续考博士,以为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就万事OK了。其实不见得如此,尤其是在艺术的范围内。在今天的社会中文凭固然不可缺,但并不是唯一一个对你一生起到关键作用的东西。你们可能不知道艺术家贝多芬和莫扎特,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出名了。莫扎特三岁的时候,就发明了三连音作品的方式,他们都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很知名的音乐家。实际上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家并没有上大学,艺术家的成就是要靠自己去创造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用一个死板的方式去学习前辈的艺术是没有用的,因为有过的艺术它就已经存在了,你还是去重复它、模仿它,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庞薰琹就讲:“ 我始终走我自己的路,我的一生是探索的一生。” 什么叫探索,就是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我在这里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父亲对我的教育。虽然我的父亲留学法国,我的母亲留学日本,他们都是中国第一代很知名的画家,但是在我的家里,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母亲,一次也没教过我如何画素描,如何画油画。在他们看来,对于孩子的教育,不能用成人的那套严谨的造型训练方法来对待,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把孩子管得很死,就会禁锢孩子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艺术教育要逐渐培养学生的个性和生动的创造活力,这条路是漫长的。
我父亲在法国巴黎的时候,全世界在那里的艺术家大约有三万多人,大多数的人是住在地下室里,生活很苦。可想而知,在巴黎那么一个地方,三万多人,要想出人头地,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巴黎繁华的地方之一是咖啡馆,学艺术的人到各个咖啡馆,不少年轻人到那里是想碰到大艺术家,比方说毕加索在这里喝咖啡,他们就靠上去,看他如何画速写,如何对景写生。
后来我父亲也开始小有名气了,所谓小有名气就是说他的画已经有人欣赏了,有人在买他的画了。当我要离开大陆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在巴黎是如何开始出名的,是因为他画了一张灰色调静物画,引来了很多圈内人的关注,逐渐有了名气。灰色调对所有的艺术家来说,是一个颇有难度的色彩,可以说世上没有几个人可以画好灰色调的画。当时那幅画画好后不久,就被一个收藏家买走了,从此以后,他就开始出名了。
你们没有学过美术史,可能不知道“ 巴黎学派” 。在法国巴黎,有很多外国人从事艺术创作而出名,他们既不像毕加索的立体派,也不像马蒂斯的野兽派,而是自由风格的一些有成就的艺术家,比如意大利的Modigliani,翻译过来叫莫迪里安尼,这类艺术家就归纳入巴黎学派,它不是一个团体性质的,但它在巴黎艺术界很有影响力。
当时有很多著名的画商找我父亲,每次去都会送一顶很贵重的贵族人戴的丝绒礼帽,那种礼帽不是一般人能够买得起的。他们希望跟我父亲签约,想把他纳入到巴黎学派来,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他的画风十年都不能变。父亲很年轻,他想,怎么能限制我十年不变呢?所以就拒绝了,因此“ 巴黎学派” 里没有中国人,之后这些画商又找到日本的一个职业学童。如果当时我父亲签下这个条约,他现在在美术史上可能就属于“ 巴黎学派” 的成员了,那样的话,他大概就留在法国,不会回国了。
在巴黎时,我父亲的想法就是自己开个人画展。办展在那个年代来说,必须要有一个权威性的评论家来替你写文章,才能够一炮而红。后来在很多外国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一个非常权威的评论家,约好在一个咖啡店里见面。到了咖啡店,那个评论家已经坐在那里等了,一见面还没等我父亲开口,他就问:“ 你几岁来巴黎的?”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突然,我父亲说他十九岁来的。老评论家又问:“ 你十九岁来巴黎,你对中国的文化到底了解多少?” 当时我父亲觉得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他带了一卷画想给他看一下,可是刚一打开来,那个老评论家就说:“ 你不用打开了,你十九岁来巴黎,在法国住了这么久,我不看你的画也知道你画的是什么样。” 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你还是回到中国去。你这么年轻,首先要对中国的文化有所了解,要有很深的了解,将来再回到巴黎开画展,到那个时候你不用来请我,我也会给你写文章的。”
同学们,你们想想,这个刺激有多大?本来是件大好事,希望开个画展、希望成功、希望一炮而红,结果请了一个评论家,自己的画连看都不看一眼,就给你懵回来了。我父亲很痛苦,想了一夜,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回国!
1930年,我父亲回来了。中国第一批艺术家到国外去留学,他们把油画这门西方艺术植入进来。植入就是引进,它不像水墨画有一两千年的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油画艺术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徐悲鸿1921年去法国,我父亲是1925年,他们就是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人。回来以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状况。徐悲鸿的艺术属于古老的、学院派艺术,我们统称为写实性艺术。而我父亲在法国时,整个法国都在近现代艺术的文化氛围中,庞薰琹、林风眠、常玉等,他们这些年轻人跟法国的美学思想是同步的,追随近现代思潮,但他们实践的途径却有区别。徐悲鸿,既是一位画家,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在国民政府控制下公费留学,所以他回国后就老老实实办起了教育。他一直是国立艺专的校长,后来又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我也是他的弟子。另外一批人是想推进中国新文化进程,在艺术上有新的道路,他们成立了“ 决澜社” ,他们的思想在当时是比较前卫、激进的。“ 决澜社” 有个声明,这个声明今天看起来也是令人非常激动,其中有一句最重要的话这样说道:“ 让我们起来吧!用狂飙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 要知道在中国传统艺术当中,基本上是水墨,是黑白的,材料也是纸张。在油画里,这个“ 色、线、形” 是一个新的概念。在那个年代,他们在一个二十五六岁,三十岁都不到的年纪,提出这么响亮的一个口号,足见我们的前辈艺术家是非常有勇气的,他们的理想非常大。
遗憾的是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整个中国处在战火中。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来认识,第一批留学的、天才的前辈艺术家,他们身处破坏性的战争年代,没有很好的条件。到了我这一代好了一些,但经过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十年时间也就浪费了。
我再讲个故事给你们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和我父亲没有住在一起。当时我非常紧张,因为我想他有些画恐怕保不住了,要被毁掉了,红卫兵要抄家。有一天,一大早我回到家里,看看屋里没人,但是听到敲敲打打的声音。我一看,我父亲躲在阳台上,蹲在那里砸什么东西,原来在砸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珠子,那个珠子很大、很漂亮,砸到最后只剩一个的时候,我说这个留给我吧。我当时也很穷,后来把它卖掉了,八十块钱。可是他在巴黎画的那些画哪儿去了呢?那些画都很好。有一张画,我现在印象很深,他画巴黎的咖啡馆,前面是一些巴黎的男人们,一个女人坐在男人的腿上,左上角有个中国人,很孤独、很苦恼,那就是他自己,那些画很大,技巧非常之好,我从小就很喜欢。我问:“ 你的画呢?” 他说:“ 昨天刚刚把裸体的画都毁掉了,就剩下现在你看到的这张头像。” 他心里在想,这张画该不会受到什么大的批判吧,就是个普通的法国老太太而已。
抗战期间,我父亲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在中央博物院工作时,他专门到云南苗族地区对民间美术进行调查。这份工作在当时来说是非常艰苦的,因为他是抱着这样的理想回国的。后来他看到很多汉代的砖,汉代的砖不像我们现在普通的砖,上面刻有很多花纹、兽纹之类的纹样。这些纹样都是从汉砖上描绘下来的。他是在透明的纸上,用很细的线,直接描绘下来的,我父亲大概描绘了上千张。他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学的时候,将这些画转借给学生看,希望他们能根据这些图像做一些装饰绘画。你们看到的这些图像,是选自他曾经编的一本《中国图案集》。记得在四川,当时我很小,大概只有七岁。英国驻中国的大使馆里有位年轻的文化人叫迈克尔•苏立文,是世界上著名的研究中国艺术的理论专家,也是英国剑桥大学、纽约大学的教授。后来这一部分的设计,他准备拿到瑞士去出版,我父亲就交给了他,大概在1945年,因为战乱,一直没有消息。迈克尔•苏立文很重视我父亲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他一直想把书出版,结果没有实现此想法,但是他保存得很好,最后完璧归赵。他想把这个设计原稿送还给我父亲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了,在座的你们还没有出生。当时他把书还回来的时候,非常新,一点损坏都没有。后来我到香港以后,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很小,印的也不好。父亲给我寄了一本,他非常的高兴,他的设计终于能够重见天日了。遗憾的是,稿子送回来的时候,到处都画满了字和线,这些原作现藏于常熟美术馆。
这些作品,你们现在看起来可能觉得很普通,但作为六七十年前到外国留学接受了新观念,并结合中国的纹样做出来的设计,就很不简单了。最右边的图片是一把伞,画得是那么细致入微。还有一部分作品是以汉代的线的造型为元素创作的。这张画的是唐代的舞蹈,他画这张线描有个鲜为人知的方法,就是先用铅笔画人体的稿子,然后直接在很薄的纸或绢下面画头、腿、衣服等人物形象元素,一气呵成。当你们看到原作时,你们会觉得很惊讶,线描怎么可以画的这么流畅、这么好,而且这么精细、完整。
我父亲在云南地区做调查时,画了很多普通苗族人的生活场景,我们来看看作品图片。在那个年代像这样题材的作品很少有前辈画家能够这么仔细地去刻画。这张画很精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苗族女孩,上山采树叶、采茶,累了坐着休息。这张画是1947年我们去庐山时画的,那个时候还是跟傅雷住在一起,我们两家的关系非常好。这张画画了三四天,一片叶子一片叶子的重叠起来,非常精细,树上的叶子色泽晶莹。
我父亲晚年在家里的时候,买不起什么花,就到处采一点花把它变成装饰性绘画的景致,像这张水仙花就是这样来的。他在晚年的时候做了些实验,颜色很少,不复杂,用最简练的方式来画。他快去世时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 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我今年有一张画,想做些尝试,只用线描来组合画面,用了两年的时间来画,我想试一试这种新的画法,看看它的艺术效果。” 所以话题又回到他手记上的一句话:我的一生是探索又探索的一生,我走我自己的路。
我们从这些图片可以看出,庞薰琹的画跟所有画家的不一样,也跟西方的艺术大师不一样,他就是他自己,这就是艺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地方。如果将来我们想成为一名画家的话,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为什么我要给你们讲关于我父亲许多的事情和故事?为什么他在法国已经初有成就的时候,而依然选择回国?他的老师、评论家劝他:“ 中国人要懂得中国的文化” ,他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最后他所留下的东西虽然不太多,但是非常有价值,这对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启发。我讲过,我父母没有教过我一笔,但是我父亲的老师怎样叫他回国这件事情对我的教育很深刻。
时间有限,讲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
活动地点:常熟市第一中学
主讲人:庞 均(庞薰琹之子、台湾艺术大学教授)
常熟美术馆根据录音整理

同学们好,我很羡慕你们,从我的视点来看,第一排到最后一排,你们每个人的脸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你们是那么的年轻、那么有活力。我想你们现在大多数应该在十四五岁之间,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年龄。相信你们都很喜欢艺术、喜欢美术,我更希望,在多年以后,在座的同学当中,有人会成为常熟的艺术家,全国有名的艺术家,甚至是世界有名的艺术家。我想,从现在开始,如果你们努力学习,逐渐进入学艺的状态,那么,这个理想是一定可以实现的。为什么?因为我想告诉你们,我是十三岁上大学,十八岁毕业,就是说我比你们现在还小的时候就进入到杭州国立艺专学习,后来变成杭州美术学院,那时像黄宾虹这些老前辈都还在世。之后我转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在我将要毕业的时候,徐悲鸿已经去世了,当时,齐白石是美术家协会的主席,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可以这么讲,当年我是全国最小的一位大学毕业生。现在我的同学已有不少去世了,活着的同学也都在八十五岁左右,或者年纪更大。我心情很不好,活着的同学越来越少了,但看到你们我就非常高兴。
到了常熟,大家多少知道庞薰琹这个名字,本来是让我用简单的方式来介绍一下,但是现在看来,《庞薰琹艺术之路的启示》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大了,用很短的时间不可能把它说得很清楚。在这里我想用一种讲故事的,比较活泼的方式来展开这个话题。希望你们听后,对自己的艺术乃至人生之路有所启示。
我父亲早已去世,如果他还在世的话,就是104岁的老人了。为什么要选《庞薰琹艺术之路的启示》这个话题呢?因为我希望通过对我父亲的著作、作品所反映艺术思想的解读,结合他的艺术之路,进一步了解、认识他的人生观,从而对我们后来的人会有所启示,尤其是常熟人。
在常熟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出现了很多有名的文人,最早的可谓孔子的弟子言子。言子在世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他四十多岁时就去世了。其实用孔子的说法,言子最像他自己,所以言子去世时孔子是非常伤心的。两千多年来,我们常熟出了很多名人,你们在座的是常熟文化发展的希望。
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介绍庞薰琹艺术之路,先看看照片吧,这就是他年轻的时候,还是在留法前后照的,大约二十多岁吧。最右边的那张比较老了,七十多岁吧,不过这个年龄可能比我现在还小一点。
我父亲是十九岁去的法国,去之前是在上海震旦医学院学习,他也是很小的年龄进大学。上海震旦学院是一个法国人办的学校,所以从一年级开始就要讲法文,我父亲从震旦学院毕业出来以后法文非常好,就到了法国。本来学医的他是应该到德国去留学,但是法国巴黎的艺术世界对他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他从小就喜欢艺术,所以后来就留在法国学习艺术了。
下面有一段简短文字的介绍,你们可以在我父亲的回忆录中看到。我取了最重要的一段话:“ 我始终走我自己的路,我的一生是探索探索再探索的一生。” 这句话,看似很平常,但却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有许多人生的故事。
前面我讲到他十九岁去巴黎,到了那以后,他非常激动,因为法国对他来讲是全新的概念,他不仅可以看到许多文艺复兴以来著名的油画原作,而且还能看到很多现代艺术设计。
我父亲在法国期间,起初是在巴黎大学学习音乐和美术,后来就想转到巴黎美术学院去。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巴黎美术学院已经开始没落了。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巴黎美术学院实际上是在学院派的没落阶段。像毕加索、马蒂斯这些人那时候已经非常有名了,就是说艺术已经由传统走向现代,但是巴黎美术学院的教育还是比较僵化的。我父亲想进巴黎美术学院去学习,被他最好的朋友常玉阻止了,他说:你现在还进巴黎美术学院?那里是学不到什么的。所以后来包括我父亲在内,他们就到艺术家的工作室游走、学习。
我们也知道,现在的社会大家都在追求一张文凭,好像从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然后读研拿个硕士学位,再继续考博士,以为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就万事OK了。其实不见得如此,尤其是在艺术的范围内。在今天的社会中文凭固然不可缺,但并不是唯一一个对你一生起到关键作用的东西。你们可能不知道艺术家贝多芬和莫扎特,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出名了。莫扎特三岁的时候,就发明了三连音作品的方式,他们都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很知名的音乐家。实际上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家并没有上大学,艺术家的成就是要靠自己去创造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用一个死板的方式去学习前辈的艺术是没有用的,因为有过的艺术它就已经存在了,你还是去重复它、模仿它,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庞薰琹就讲:“ 我始终走我自己的路,我的一生是探索的一生。” 什么叫探索,就是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我在这里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父亲对我的教育。虽然我的父亲留学法国,我的母亲留学日本,他们都是中国第一代很知名的画家,但是在我的家里,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母亲,一次也没教过我如何画素描,如何画油画。在他们看来,对于孩子的教育,不能用成人的那套严谨的造型训练方法来对待,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把孩子管得很死,就会禁锢孩子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艺术教育要逐渐培养学生的个性和生动的创造活力,这条路是漫长的。
我父亲在法国巴黎的时候,全世界在那里的艺术家大约有三万多人,大多数的人是住在地下室里,生活很苦。可想而知,在巴黎那么一个地方,三万多人,要想出人头地,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巴黎繁华的地方之一是咖啡馆,学艺术的人到各个咖啡馆,不少年轻人到那里是想碰到大艺术家,比方说毕加索在这里喝咖啡,他们就靠上去,看他如何画速写,如何对景写生。
后来我父亲也开始小有名气了,所谓小有名气就是说他的画已经有人欣赏了,有人在买他的画了。当我要离开大陆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在巴黎是如何开始出名的,是因为他画了一张灰色调静物画,引来了很多圈内人的关注,逐渐有了名气。灰色调对所有的艺术家来说,是一个颇有难度的色彩,可以说世上没有几个人可以画好灰色调的画。当时那幅画画好后不久,就被一个收藏家买走了,从此以后,他就开始出名了。
你们没有学过美术史,可能不知道“ 巴黎学派” 。在法国巴黎,有很多外国人从事艺术创作而出名,他们既不像毕加索的立体派,也不像马蒂斯的野兽派,而是自由风格的一些有成就的艺术家,比如意大利的Modigliani,翻译过来叫莫迪里安尼,这类艺术家就归纳入巴黎学派,它不是一个团体性质的,但它在巴黎艺术界很有影响力。
当时有很多著名的画商找我父亲,每次去都会送一顶很贵重的贵族人戴的丝绒礼帽,那种礼帽不是一般人能够买得起的。他们希望跟我父亲签约,想把他纳入到巴黎学派来,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他的画风十年都不能变。父亲很年轻,他想,怎么能限制我十年不变呢?所以就拒绝了,因此“ 巴黎学派” 里没有中国人,之后这些画商又找到日本的一个职业学童。如果当时我父亲签下这个条约,他现在在美术史上可能就属于“ 巴黎学派” 的成员了,那样的话,他大概就留在法国,不会回国了。
在巴黎时,我父亲的想法就是自己开个人画展。办展在那个年代来说,必须要有一个权威性的评论家来替你写文章,才能够一炮而红。后来在很多外国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一个非常权威的评论家,约好在一个咖啡店里见面。到了咖啡店,那个评论家已经坐在那里等了,一见面还没等我父亲开口,他就问:“ 你几岁来巴黎的?”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突然,我父亲说他十九岁来的。老评论家又问:“ 你十九岁来巴黎,你对中国的文化到底了解多少?” 当时我父亲觉得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他带了一卷画想给他看一下,可是刚一打开来,那个老评论家就说:“ 你不用打开了,你十九岁来巴黎,在法国住了这么久,我不看你的画也知道你画的是什么样。” 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你还是回到中国去。你这么年轻,首先要对中国的文化有所了解,要有很深的了解,将来再回到巴黎开画展,到那个时候你不用来请我,我也会给你写文章的。”
同学们,你们想想,这个刺激有多大?本来是件大好事,希望开个画展、希望成功、希望一炮而红,结果请了一个评论家,自己的画连看都不看一眼,就给你懵回来了。我父亲很痛苦,想了一夜,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回国!
1930年,我父亲回来了。中国第一批艺术家到国外去留学,他们把油画这门西方艺术植入进来。植入就是引进,它不像水墨画有一两千年的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油画艺术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徐悲鸿1921年去法国,我父亲是1925年,他们就是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人。回来以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状况。徐悲鸿的艺术属于古老的、学院派艺术,我们统称为写实性艺术。而我父亲在法国时,整个法国都在近现代艺术的文化氛围中,庞薰琹、林风眠、常玉等,他们这些年轻人跟法国的美学思想是同步的,追随近现代思潮,但他们实践的途径却有区别。徐悲鸿,既是一位画家,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在国民政府控制下公费留学,所以他回国后就老老实实办起了教育。他一直是国立艺专的校长,后来又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我也是他的弟子。另外一批人是想推进中国新文化进程,在艺术上有新的道路,他们成立了“ 决澜社” ,他们的思想在当时是比较前卫、激进的。“ 决澜社” 有个声明,这个声明今天看起来也是令人非常激动,其中有一句最重要的话这样说道:“ 让我们起来吧!用狂飙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 要知道在中国传统艺术当中,基本上是水墨,是黑白的,材料也是纸张。在油画里,这个“ 色、线、形” 是一个新的概念。在那个年代,他们在一个二十五六岁,三十岁都不到的年纪,提出这么响亮的一个口号,足见我们的前辈艺术家是非常有勇气的,他们的理想非常大。
遗憾的是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整个中国处在战火中。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来认识,第一批留学的、天才的前辈艺术家,他们身处破坏性的战争年代,没有很好的条件。到了我这一代好了一些,但经过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十年时间也就浪费了。
我再讲个故事给你们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和我父亲没有住在一起。当时我非常紧张,因为我想他有些画恐怕保不住了,要被毁掉了,红卫兵要抄家。有一天,一大早我回到家里,看看屋里没人,但是听到敲敲打打的声音。我一看,我父亲躲在阳台上,蹲在那里砸什么东西,原来在砸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珠子,那个珠子很大、很漂亮,砸到最后只剩一个的时候,我说这个留给我吧。我当时也很穷,后来把它卖掉了,八十块钱。可是他在巴黎画的那些画哪儿去了呢?那些画都很好。有一张画,我现在印象很深,他画巴黎的咖啡馆,前面是一些巴黎的男人们,一个女人坐在男人的腿上,左上角有个中国人,很孤独、很苦恼,那就是他自己,那些画很大,技巧非常之好,我从小就很喜欢。我问:“ 你的画呢?” 他说:“ 昨天刚刚把裸体的画都毁掉了,就剩下现在你看到的这张头像。” 他心里在想,这张画该不会受到什么大的批判吧,就是个普通的法国老太太而已。
抗战期间,我父亲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在中央博物院工作时,他专门到云南苗族地区对民间美术进行调查。这份工作在当时来说是非常艰苦的,因为他是抱着这样的理想回国的。后来他看到很多汉代的砖,汉代的砖不像我们现在普通的砖,上面刻有很多花纹、兽纹之类的纹样。这些纹样都是从汉砖上描绘下来的。他是在透明的纸上,用很细的线,直接描绘下来的,我父亲大概描绘了上千张。他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学的时候,将这些画转借给学生看,希望他们能根据这些图像做一些装饰绘画。你们看到的这些图像,是选自他曾经编的一本《中国图案集》。记得在四川,当时我很小,大概只有七岁。英国驻中国的大使馆里有位年轻的文化人叫迈克尔•苏立文,是世界上著名的研究中国艺术的理论专家,也是英国剑桥大学、纽约大学的教授。后来这一部分的设计,他准备拿到瑞士去出版,我父亲就交给了他,大概在1945年,因为战乱,一直没有消息。迈克尔•苏立文很重视我父亲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他一直想把书出版,结果没有实现此想法,但是他保存得很好,最后完璧归赵。他想把这个设计原稿送还给我父亲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了,在座的你们还没有出生。当时他把书还回来的时候,非常新,一点损坏都没有。后来我到香港以后,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很小,印的也不好。父亲给我寄了一本,他非常的高兴,他的设计终于能够重见天日了。遗憾的是,稿子送回来的时候,到处都画满了字和线,这些原作现藏于常熟美术馆。
这些作品,你们现在看起来可能觉得很普通,但作为六七十年前到外国留学接受了新观念,并结合中国的纹样做出来的设计,就很不简单了。最右边的图片是一把伞,画得是那么细致入微。还有一部分作品是以汉代的线的造型为元素创作的。这张画的是唐代的舞蹈,他画这张线描有个鲜为人知的方法,就是先用铅笔画人体的稿子,然后直接在很薄的纸或绢下面画头、腿、衣服等人物形象元素,一气呵成。当你们看到原作时,你们会觉得很惊讶,线描怎么可以画的这么流畅、这么好,而且这么精细、完整。
我父亲在云南地区做调查时,画了很多普通苗族人的生活场景,我们来看看作品图片。在那个年代像这样题材的作品很少有前辈画家能够这么仔细地去刻画。这张画很精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苗族女孩,上山采树叶、采茶,累了坐着休息。这张画是1947年我们去庐山时画的,那个时候还是跟傅雷住在一起,我们两家的关系非常好。这张画画了三四天,一片叶子一片叶子的重叠起来,非常精细,树上的叶子色泽晶莹。
我父亲晚年在家里的时候,买不起什么花,就到处采一点花把它变成装饰性绘画的景致,像这张水仙花就是这样来的。他在晚年的时候做了些实验,颜色很少,不复杂,用最简练的方式来画。他快去世时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 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我今年有一张画,想做些尝试,只用线描来组合画面,用了两年的时间来画,我想试一试这种新的画法,看看它的艺术效果。” 所以话题又回到他手记上的一句话:我的一生是探索又探索的一生,我走我自己的路。
我们从这些图片可以看出,庞薰琹的画跟所有画家的不一样,也跟西方的艺术大师不一样,他就是他自己,这就是艺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地方。如果将来我们想成为一名画家的话,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为什么我要给你们讲关于我父亲许多的事情和故事?为什么他在法国已经初有成就的时候,而依然选择回国?他的老师、评论家劝他:“ 中国人要懂得中国的文化” ,他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最后他所留下的东西虽然不太多,但是非常有价值,这对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启发。我讲过,我父母没有教过我一笔,但是我父亲的老师怎样叫他回国这件事情对我的教育很深刻。
时间有限,讲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