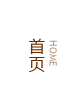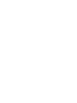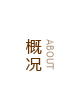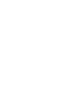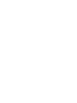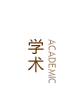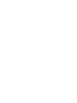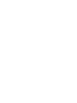文心的综合——中国画
2010-04-02 01:27:00来源:庞薰琹美术馆点击:8369
活动时间:2010-4-2
活动地点:常熟美术馆报告厅
主讲人:王玉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常熟美术馆根据录音整理

我想谈谈这个题目为什么叫《文心的综合》?这是我对中国画的一种感悟。举个例子,清华美院建院50周年、同时也是纪念庞薰琹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学院举办了5个展览,是我们学校几个非常权威的老师的展览,有的在世,有的已经过世,他们是祝大年、张仃、吴冠中、袁运甫和庞薰琹。展览办得非常成功,每个人的风格不同,画法、追求的方向也有很大差异。大家看完展览,心里有种非常强烈的体会:庞先生的画最好!为什么?仔细思索一下,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 文心” 的问题,庞先生的画体现了一种文化特性,有文化内涵。当然不是说别的老师的画没有文化含义,而是说庞先生最接近我个人心中“ 中国文化” 的含义。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今天有幸在常熟— — 庞先生的故乡来谈这个问题。
很多人对于中国画有这样的观点:中国画太单调,中国画本身对人的刺激强度不够,中国画的外在内容太多,有段时间我也是这个看法。1995年从法国回来后,我感觉中国画强力不够,放在一个环境里面,感到它很弱。在大英博物馆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线很细,没有震撼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其实看画需要一个氛围。在一个空间里可能会感到某些画较弱,但古人的画很多是藏在袖子里拿出来共同欣赏的,距离都在一米左右,在这个空间里欣赏是最适合的,如果它放到一个庙堂里面自然就显得弱了。有的画内容是人物和山水,高四米,气势就很强,所以看画需要制造一个氛围,就像喝茶一样,喝大碗茶,那是解渴,喝完就完了,但你要品茶的时候,最好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细细地一点一点地品,功夫茶是要一点一点地品味,和解渴没有关系,它偏重于审美。我想为什么要像喝大碗茶那样去看中国画?为什么要放在一个不应该放的环境里面?能不能制造一个氛围,品读中国画的氛围?我提出我的看法,我觉得绘画更是一个文化形态,强调刺激感、现实性、时间性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画画不像时装那样,过了这个季就没用了,变成垃圾给扔掉,绘画应该研究最内在的核心,能够永恒的核心。我有一个体会,中国画最强调文化形态,在世界上也是唯一以文化综合为标准的绘画。欧洲的绘画不强调文化形态,中国画有“ 诗、文、书、印” 好多内容,有人说那些没用,是外在的,但是我认为如果运用得很好,会变成非常好的内容。比如像郑板桥、潘天寿,他们在文字和绘画的结合关系上运用的非常好,体现出人的品格。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决定,画的价值与画得“ 像不像” 没有关系,这就是文化心理。有意思的是,中国绘画在五代以前基本没有分行的,没有文人和工匠的区别,是以人物画为主的时代。西洋画派没有专门的划分,在18世纪末才出现了风景画或印象派等等。中国人有一种文化心态,因为中国强调文化,文人是主体,当官的都是文人,不像西方的画家是雇佣的工匠,绘画内容是宗教性的,为宣传宗教服务,用宗教来维持现在和警示未来的意思。但是中国画恰恰相反,尤其是中国山水画是远离这一切的,甚至是鄙视现实的心态。严格说起来应该在二到三世纪左右形成,建安时期国家很乱,出现了曹操这样的人物,人们生活很悲苦,思考人生去向问题,所以当时人的心态包括那时的艺术形式是对人生的感叹。曹操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的《长叹歌》里都是哀歌,歌颂死亡,中国人偏向这种歌曲。后来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她的哥哥长孙无忌就是以唱悲歌而闻名,他唱的是送葬歌。那时候的人对人生产生了很多感叹,由此出现两种形态:一种是特别入世的,像曹操这种人,罢黜百家,自己来做一些对人民有用的事情;另一种是闭世的状态,就是一百多年后东晋时候最盛行的,他们感觉到自己无力便躲开这些矛盾。当道教和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人们就找到一种媒介躲开社会矛盾。但是躲开社会矛盾得有条件,就像鲁迅讲的,陶渊明也是要吃饭。因为躲开社会,人物画被慢慢淡化,中国山水画出现了。当时出现很多歌颂自然的诗,不是针对人,是针对自然。这种形式由于文人的推动慢慢变成为主流,在五到六世纪,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文人,叫刘勰,他写过一本书《文心雕龙》,强调文章的写法、文字的形式、文字的分类、修辞的方式,最强调的是思路问题,就是作文中要有一个思想内容。不到几十年,就出现了谢赫的《六法论》,当时还没有山水画,《六法论》主要是针对人物画的。中国文化品位就像道教一样,像老子的观点,有一个很大的涵度,慢慢就演化为中国画的品类,成为所有形式的一个标准,就是现在讲的“ 六法” ,用气韵生动来表现山水,实际上当时最早是评判人物画的。从那时起,中国的文人就慢慢登上了中国绘画的舞台,慢慢地由山水文化走向山水艺术。但真正提倡文人思想的人,实际是四世纪的苏东坡,一千年以前他主动提出了文人画的要求:“ 我看画就像看天下的马一样,我看过了一千匹马就明白了马的好坏,然后我翻阅工匠的画,我一看就倦,但是我看文人画的时候,我就来精神了。” 他看到有思想的画的时候就来精神了,说明一个问题:绘画要有思想。以前的工匠大部分是被雇佣的,是按照客户要求来画的,没有权利和思想。文人不靠绘画吃饭,不在乎这个,就产生了自由的想法。同时又有个问题,就是技术的问题,比如郭熙,他是北宋的宫廷画家,没有多少文化,但他的绘画本事却很大,画得非常好,在临死以前由他儿子整理完成了《林泉高致集》。苏东坡多次在诗文里谈到郭熙,说他画得如何好,如何有文气,这好像和他的原意相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苏东坡是重视技术和思想的,首先重视思想,然后重视技术。山水画成为中国绘画主流是到南宋时期,他代表中国的一种思想,中国人慢慢离开了现实,走向了自然。画山水画的人基本都是文人,工匠很少,中国艺术还有个特征就是民族和民间的问题,这是一个矛盾。民间是民族的一部分,但是中国画的主流尤其在近700年,山水占主体,通过很微弱的信息,表达文人对自然的留恋,对现实的逃避,元代最明显。当然有很多画家兼有两方面,比如元代初期赵孟頫,应该说他是最保守的,也是最先进的,既有宫廷画家的功力,又有文人的情思。画画的时候和写书法相联系,这是文人的优势,赵孟頫第一次把绘画和书法放在同一个位置上。在他之前,一幅画的题字都是很小的,甚至不题字。从赵孟頫开始,经常会把绘画和书法放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赵孟頫的理论又是讲古法的,他说:“ 我的书法不看宋人也不看唐人,是看晋人,我的画法是看唐人。”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我们研究下来,唐代以前的书法折笔用得很少,气韵比较连贯;宋代、唐代以后的书法,折笔用得较多,横划很细,竖划特别粗,不是圆笔法,比较强调工艺性,晋代书法就不是这样。赵孟頫书法上学晋人,但实际创作行为上不是这样。所以有时候看一个艺术家,不要看艺术表面的东西,画得很旧,实际上旧的里面蕴藏很多新的生机。比如现代欧洲写实画家佛洛依德,他有时候突然回归到古典方法,但他的作品还是表现出新意,证明不在于表面的形式,而在于思想方式,这个就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道理。在欧洲的绘画历史上一般强调“ 像与不像” ,明暗关系“ 准与不准” ,特别强调真实性,这个理论来源是达芬奇的“ 镜子说” ,说看到这个对象就像看到镜子一样。而中国人不是这个观点,中国人认为“ 镜子观点” 是空洞的,中国传统绘画中从来没有强调这种所谓的真实。中国画像浮雕,像虚光的照片,本身不强调立体,虽然也注意到了光线和影子却从来不画倒影,这种讲法不完全对。顾恺之讲:“ 山有影,景物皆倒置。” 他的画没看到,但有文字记载,他绝对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也注意到了色彩。为什么归结到最后中国画会成为这种形态?我觉得中国画正是依靠你的这种视觉经验来完成你对绘画的理解。比如画一个月亮,勾一下线,并没有画出月亮的颜色,照你的经验理解为月亮,一看就是个月亮,靠你的识别经验启发你去识别,欣赏者和作者共同完成识别关系。它不是淋漓尽致的,淋漓尽致是栩栩如生的概念。它是用你的文化背景来理解它,完成这个审美过程,如果不够的话,就加以诗句来帮助你理解,不懂中国诗歌、不懂中国诗情的人是很难理解中国画的,这是修养问题。所以国外很多人说,看你们中国人画画用一些墨水涂来涂去,他不理解,就像我们不理解欧洲人的现代绘画,拿着一个桶泼洒颜色,泼到什么效果就是什么效果,那不是胡乱画嘛!这是文化的差异,我们没有这个文化背景。中国人需不需要理解西方人的文化背景·需不需要服从西方人的文化背景?这是个问题。
上午看了破山寺的寺院,我特别感动,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园林建筑了,真是很美。中国人非常理解,其实外国人也非常理解,这种差异性体现得非常明确,就是一种文化新意,就是一种文化审美。我们去过欧洲,去过西班牙、法国,看他们的园林简直像蛋糕一样,一片一片的,树修得像皮球一样圆,每个季节修一次。在我们看来实在太傻,其实树本来就很美,他们的愿望是把它们归一、整齐,把树弄成圆球形,在中国人看来这简直是暴敛天物,完全把它的灵性给弄没了,这就是文化差异。但是我认为不要缩小这种差异,应该保持自己的审美。北京城九个城门如果都保留下来的话,那简直太伟大了,因为建设问题给破坏了,永远不可能恢复了,这是很难受的。有时候审美就表现在文化差异上,你没有权利去强迫西方人理解你,你也没有必要按照西方人的方式来对待中国的艺术和中国人的文化形态,应该保持自己优美的东西,保持自己品功夫茶的那种感觉,而不是只为了解渴。这么说起来好像中国绘画没有现实主义似的,实际上还是有的,是体现在文化形态和浪漫心态上。中国古代很多诗歌就是这么表现的,那时可以用诗歌来汇报工作,汇报工作都能是艺术性的,多么可贵!那些奏折的文采都非常好,帝王一看就能理解,用词都很雅很讲究,绝不会出现粗暴的词句。这种文化应该保留下来,但现在都做不到,都按照公文的形式来做。
再讲中国画的“ 综合” 问题。诗、书、画、印是中国画的特征,还要看你怎么运用。也有一些运用不好的例子,比如说《富春山居图》,当时乾隆皇帝看到这幅画很激动,他的审美有限,但其实是一幅假画。他特别喜欢表现,把画带在身边,一有空就题上一首诗、题上一篇文章,一共题了53次,画面给题满了,完全没有空间了,把那画卷变成书卷了。后来发现了真迹,一看当然比假的画得好多了,但皇帝不能有错,他就在真迹上再题几首诗,最后压一个章,意思是比我题过的那个差一点。皇帝题字是显示权利,他往往不管画面的情况,甚至弄个大印盖在中间— — “ 御览之宝” ,有时像个大饼一样的糊在上面,很丑。画家就很少这样做,很少把自己很好的画面题字搞坏,除非他不是一个文化人,画家都题得很适当,因为他有审美能力。如果有点文采的话,题首诗在上面,加强对画面意境的理解,变得更完整、更美,这种结合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形式。郑板桥的画,他的石头是勾法,没有皴法,但能感觉到很厚重,这是最了不起的地方。“ 薄” 与“ 厚” 是艺术表现的两种形态,有时候他在大石头上写上一大片的字来填补空间,切割空间关系,使画面丰富有层次,把字当做画面的一部分,他是有艺术修养的人,结合得非常好,使不完美的东西变得很完美。潘天寿也是这样,他有时候故意找长线来题字,一根线拉得很长,再找另外一根线,求共性,叫“ 同形反复” ,搞摄影的都知道,一个形放大或缩小,反复出现时会产生统一。潘天寿甚至把一个东西故意强化成一个形,使画面的内容统一起来,有时感觉画面单薄,要加一条线的时候,他故意漏掉几个字,再加上一行小字补充这个空间,煞费苦心,很了不起。我看塞尚的画,塞尚早期的画很笨,很傻,后期他干脆歪打正着,反正画不准,就在画面上切割结构、研究形式,结果造就了一代大师,成为“ 立体派” 的开山之祖。人在长期磨练之后会突然产生一种自然的感觉,塞尚就是这样,他老画对面的山,天天在画,把山画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再切割面的关系,画得非常有意思。他不知道自己多伟大,当时莫奈拉着他去见罗丹,他的腿都软了,差点给罗丹跪下,他不知道自己比罗丹还要伟大。画能体现一个人的性格和人格,比如咱们看潘天寿的画,你能感觉他和你有距离,他是很孤傲的一个人,他的画也和你有距离,他的画体现那种高傲、“ 不可亵玩” ,体现他本身的性格。同样,像李苦禅先生,和他只差一岁,关系也很好,互相也有影响,但苦禅老人的画里面有一种朴实,是内在的醇厚的情感,和潘天寿完全不一样。虽然表面看他们的画很像,画的内容也差不多,但是能找到他们心里的那种差异。能找到和别人的差异,在绘画中这点很重要。我们学画时,往往会说我们像谁像谁,但到了一定时候,要做到我不像谁,一定不能像谁,要找到自己,找到真实的自己,找不到真实的自己,往往会走向歧路。和潘天寿同时期的画家张书旗,他原来是画大写意的,吴昌硕那路,画得像极了,后来他觉得不是那回事,最后他用色纸画和平鸽,最有名的作品是中国政府献给罗斯福的《百鸽图》,用色纸和白粉画的一百多只和平鸽,这就是真正的张书旗,他找到真实的自己,就有价值了。王个移的画学得特别像吴昌硕,看得一点意思也没有,这很悲剧。王雪涛先生也是这样,学齐白石学得像极了,齐白石说:有人能学到我的心,但没有人能学到我的手,只有雪涛能学到我的手,和我的一模一样,我自己都分不出来。但是最后王雪涛还是转向了,转向他自己,慢慢地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在北方他的小写意价格一路上升,已经达到几十万了,接近齐白石水平,他的价值被认同了。假如还跟着齐白石走,那他就没有任何价值,也不可能有价值。所以说要善于找到自己,根据自己的文化,根据自己的体验来找到自己。
再谈一下关于“ 印” 的问题。中国印的历史很长,从战国开始就有玺印,盖图章叫落款,阳为款(鼓起来的字叫款),阴为识(凹进去的字叫识)。发展到战国变成官员行使权利的象征,就是官印。文人用印的时间,严格说来是从赵孟頫开始的,赵孟頫自己并不刻印,他的印都是自己写好后找工匠刻的,有水晶的,有象牙的,那时还没有石印。真正刻印是从明代开始,赵孟頫作为中国第一个把书法放到绘画位置上的人,他很看重图章,他的图章都是自己设计的。当时的印泥不是油印,而是水印。咱们有时候看古画的时候,临假画的人会把现代印泥盖上去,盖在宋画上,我们一看就乐了,明显是假的,那时候根本没有印泥。像《五牛图》,我临过,知道上面有四十多个图章,就是水印,这是一个常识。印泥是到了明代慢慢调制成的,文人介入以后,产生各种流派,包括咱们常熟的“ 虞山派” 篆刻家赵古泥。印章是以耐看、浑厚、协调为目的的一种形式,是表现画面文化心态的一种重要形式。咱们还有很多传统,比如印泥有各种颜色,写挽联时盖蓝色印泥,现在很多人都盖红图章,过去是不允许这样的。有很多形式咱们可以利用和发展,包括图章。图章内容很多,有自己的志向,有自己的名号,对画面起到调节作用。毛泽东的书法从来不盖图章,别人给他刻了,他也不盖。作为画家来讲,我觉得图章是很重要,有一个女书法家提出:书法家也要写诗。虽然看她诗写得很差,还不如抄古人的诗,但是懂一些诗还是好的,对画的理解有好处,所以画面还是要注意文气。
再谈谈“ 中西” 问题。我认为中国画讲究文心,并不排除西洋画的文化气息,但是我反对一个观点,说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人在文化上绝对不可以这样的。比如说吃面包的人,怎么来理解喝豆汁的?生活地理环境和视觉习惯不能强同,也不可能强同。绘画属于视觉范畴,必然有最基本的视觉内容,如果没有视觉内容就失去了本身的价值。像现在有人搞音乐,到台上演奏的时候,一个人站着,一句话不说,过了二十分钟走了,说完成了,他就是老子的观点:大音希声— — 你自己怎么想象,你自己理解去吧。这就太虚无主义了,是离开了艺术形式所要求的基本内容。既然属于视觉艺术,就应该有视觉艺术的基本内容,同时要注意它所限定的视觉范畴的规律。民间绘画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有的很强烈,很亮,很有冲击力。所以有很多西方人看到中国的民间艺术非常激动,包括京剧,尽管听不懂,但具有典型特征,五颜六色的人在舞台上晃来晃去,很有意思。民间的艺术保留着自觉的原始的东西,这东西应该吸收。实际上,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很多好东西被文人所吸收了,比如敦煌莫高窟第220窟,我觉得画得太好了,一查时间,比阎立本的《帝王图》还要早;还有《维摩诘图》,比吴道子还要早,还要好。在古代也有个互动关系,不要蔑视传统的东西,有些被认为是最通俗的,其实在最通俗的事情当中也可以找到一些很有趣的表现内容。像明末清初的陈老莲,他把很多装饰性的元素运用到画上去,当时苏州地区的画家吴斌就是专门用装饰形式来表现平面构成关系,他吸收了很多中国民间的东西,中国民间大有可取的内容。我们看到吴冠中先生的画中用很多品色,像紫罗兰、桃红,一看很刺激,细细一品,真好,用色真好,非常强烈。他画面的内在内容并不缺乏,加上色彩,更强化了,非常有现代视觉感。文化是多元的,吸收可以从民间、民俗,可以从东方、西方,但是中心内容应该保持,应该保持中国的文化心理。
再谈一谈我个人的绘画。朋友们刚才看到我的展览,其中有很多造像,有很多人问我是什么原因画这些的?我说我并不是佛教徒,并不信仰宗教,只信仰“ 美” ,我觉得造型本身是一种无言的表达方式。比如我们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会感觉她在注意你,《蒙娜丽莎》为什么会成为经典?是你看她的时候,有多种涵盖因素在里面,你看她笑,其实没在笑,但细看好像又在笑,他的“ 度” 把握得特别好。我在中国传统造像里面看到这个元素,尤其是北魏造像,你用什么心情看她的时候,你都能得到一种回应,和你有一种互动关系。他的“ 度” 把握得很好,绝不会出现过于悲和过于喜的状态。很多搞雕塑的人临摹这些东西就是临不出那种感觉,要么过了,要么不够,程度非常难把握。这就说明,传统一旦过去以后,你想恢复它,没有那种心态是恢复不来的。就绘画来讲,每个画家都想向前推进,我认为,在推进的时候应该多加强对文化的理解,不要做表面文章,你要通过你自己找到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恰不恰当,需要时间来考验。只有通过写生才能找到那种生命的活力和真切的感受,如果你反复重复一个题目会感到很贫乏,你必须要从自然中找到一种新的生命力。像吴冠中先生,六七十岁了还去写生,非常了不起;张仃先生八十多岁的时候,我还陪着他去写生,他是从自然当中吸取一种真切的感觉。张仃先生已经过世了,在他去世前的十年,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他不画画了?因为他离开了对环境的真实感受,就不愿意来造这些东西了。他不虚伪,他必须从自然中吸取,不然他宁可不画,他的画里有一种内在的气质。有人说张仃先生的画有气而无韵,但我感觉这气本身就来自于韵。他那种情绪不是婉约的,绝对是北方人那种强悍的情绪。大家应该多从自然文化中吸取内容,找到自己的语言。中国文人往往强化修养,很多人都说只要字写得好,画就画得好,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常熟最有名的书法家翁同龢,字写得好极了,非常有厚度,很了不得的“ 庙堂字” ,按理说他的画也应该画得很好,但是我看过他的画,差极,不知道怎么会画得那么差,就是说,书法和绘画是两回事,造型是造型的问题,笔墨和造型没有直接的关系。他没有像潘天寿和齐白石那样,将两者融合得那么完美,造型感是需要用很大的功夫来训练的。
我的总体观点就是:文化本身就是中国绘画艺术的一个内容。文化是立体的,包括多种内容,历史、哲学、书法、音乐各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本身对绘画是有帮助的,大家不要忽略了画外的修养。当然更重要的是画的内容,你有很强的造型能力,才能把自己的愿望表达出来,然后加强素养,加强文化。我从庞先生的画中就体会到这点,这就是我对中国画的总体认识。
主持人:
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王老师提问。
提问者1:
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您怎样处理写生和创作的关系?要不要采用照相机来作为辅助工具?
王玉良:
写生和创作的关系,有时候是这样的,我家人说我,怎么画了那么多的写生都不用到创作中去,不都白费了吗?我感觉它们有矛盾关系,写生为什么重要?不写生就没有一种体验,就像日记一样,你记的日子忘不了,没记的日子好像不存在了,只有画过以后才有一种体验。拍照片也是一种写生手段,但写生和照片完全是两回事,拍照片过后慢慢就淡化了,但写生会好一点。我画过莫高窟,记得1989年举行一个展览时,我翻阅过去的东西,翻到十年前的速写,想到莫高窟夜晚的月亮,就根据写生的感觉把它提炼出来。莫高窟其实挺高的,还有水塔什么,高低起伏,但我当时的感觉它是沙漠,平常如水,所以我画成平。当时我画了个黑月亮,有人写了文章说什么心态?实际上只是视觉形象,以视觉经验来理解这个东西,人家误以为是月亮。写生和创作是相辅相成的,有时候用得上,有时候用不上,经过写生后体会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写生也有缺点,写生有个概括的过程,有一次我在重庆画桥、木阁楼,一开始我坐在那里,画了整整一天,一个个房子画过去,结果画完以后看,却不是那么回事,我画得那么真实,怎么就出不来效果?第二天我干脆坐在那先画线,画完线往里填内容,感觉就不一样了。写生是概括的,就像我们去西藏,看到上面雪山,下面菜花、森林,多好看啊!可是下车去找却找不着,不是找不到,而是有距离,在形式中重叠了,写生时需要组合关系。
提问者2:
王老师我想问一下,中国画侧重于文学性,西方绘画注重求真写实。现代中国画家比如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驰名中外。中国画在以后会向一个什么方向发展?会不会保持一种静态的趋势?
王玉良:
绘画从近代来讲,像林风眠、徐悲鸿等都走向西方,并从中吸收了很多好东西。去西方的人很多,但是成功者并不是太多,像林风眠是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个画家,因为和他自己的文化心理结合得比较好。有的画家把西方的东西搬过来显得比较生硬。西方绘画很有哲理,现在这种东西差异慢慢被世界所共同认识。举个例子,意大利有个画家叫莫兰迪,西方人称他为“ 洋八大” ,他把一个内容反复画,把内容扩展成无限的思想。他画瓶瓶罐罐,把它们看成是活的生命,看成各种组合方式、各种构成方式,他只是画瓶瓶罐罐,什么方法都用过,在他的瓶瓶罐罐中,整个西方美术史全部包括了。这个画家是很自闭的一个人,一生没有结婚,老在一个小城不出去。在同一个内容中,在反复描写对象中,他发现了不同的表现方式和不同的思想内容。莫兰迪在西方被推崇得很高,大家都认识到他的文化价值,实际上他的思想核心和东方的“ 八大” 有联系。“ 八大” 画荷叶,通过荷叶表现各种形式和组合方式,表现各种不同的思想情感。徐悲鸿、林风眠等等,他们有不同的社会经历,表现的内容是不同的。徐悲鸿有很强的写实性,他曾经骂过很多西方现代画家,他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国人当时还没有一个人能达到徐悲鸿的写实能力,我翻阅画册,徐悲鸿的素描人体画得实在太好了,比起西方大师一点都不逊色。他只活了58岁,画出那么多画来,很惊人。他中西结合得很好,他的书法写得那么天然,就单从书法方面,在当代画家中也只有齐白石可以和他相比,那种个性,那种醇厚,那种美感,值得肯定。徐悲鸿本身有点偏执,但是当时中国历史需要这么一个人,如果没有徐悲鸿,还会有别的人出现。历史就是这样,总有人要踏上那一步,后人才能跟上去。而林风眠没走那条路,他走的是近代艺术的路,细细看他的画,你就可以体会到他画的中国味道,一个画西画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画中国画的。就像最近抽象画家朱德群的展览,一看就是中国人画的,那种感觉和西方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他也套用西方那种形式,但核心是中国画。就像一个南方人和一个北方人,纵然这个南方人长得很粗犷,北方人长得很秀气,但在具体处事上,一看就知道他们的差异。至于刘海粟,只能算一个教育家,本身的艺术不是很成熟,他都在别人的范畴里面做,没有自己个人的格局,包括书法。林风眠则是打通了很多关系,一个是打通了中西的关系,再一个是打通了民间和文人的关系。他的画文化性强,面很宽,不是局限于绘画本身,文化修养是成就一位大师的重要方面。可能跟他接触的教育和老师有关,他所接触的内容很宽泛,所以他开创了这么一条路。这条路后来发展了很多人,像赵无极、吴冠中先生都是这个系统的。这个文化系统实际上是对中国绘画推进最大的一个系统,包括李可染。你细看李可染《爱晚亭》的逆光效果,一般人觉得李可染绘画像黄宾虹、齐白石,我感觉林风眠的成份最多,无论从视觉形式和审美感觉。李可染画的那种压抑的感觉、有挣扎的感觉、带着苦涩的感觉,和林风眠完全是一致的,他的画里很压抑,没有太多的欢乐,不是山花烂漫,骨子里的审美和林风眠在一起。比如说黄宾虹到了晚年,完全是返老还童了,他的画是山花烂漫的,还有齐白石,非常有生命力,是那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但在林风眠、李可染的画里没有这种感觉。
关于动态还是静态,刚才那位同学说“ 西方是动态的,中国是静态的” ,这个不一定,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西方的动态有时是不节制的,特别疯狂,有些近代的西方油画家,包括毕加索的画都有这种内容,带有疯狂的、下意识的。中国画也有下意识,但是有约制感,不能说“ 中国人是静态的” ,其实是一种文化约制。中国画的走笔,讲究“ 有没有来处” ,像陆俨少的一笔下去,感觉线的走笔是连笔的,接笔的时候捻一下,收锋,这个线非常耐看。像李可染画的牛,一看就知道,没有几年功夫根本就画不出这道线来,像刀切一样入木三分,他的收笔是捻的,这是个用笔技巧问题,是和书法的结合问题。中国近代的四个大画家,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都属于“ 金石派画家” 。所谓“ 金石派” ,就是他们和篆刻、书法结合最密切,笔法非常耐看,单独看都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当然,这取决于中国人,写过书法的人一看用笔,就知道他写过什么,学过什么碑,写过“ 二王” 、“ 文徵明” 等等。中国画是讲究这个的,黄宾虹走笔时那种盘旋的感觉,那种悲欢离合都能体验到,这就是绘画在“ 像” 以外有内容。
活动地点:常熟美术馆报告厅
主讲人:王玉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常熟美术馆根据录音整理

我想谈谈这个题目为什么叫《文心的综合》?这是我对中国画的一种感悟。举个例子,清华美院建院50周年、同时也是纪念庞薰琹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学院举办了5个展览,是我们学校几个非常权威的老师的展览,有的在世,有的已经过世,他们是祝大年、张仃、吴冠中、袁运甫和庞薰琹。展览办得非常成功,每个人的风格不同,画法、追求的方向也有很大差异。大家看完展览,心里有种非常强烈的体会:庞先生的画最好!为什么?仔细思索一下,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 文心” 的问题,庞先生的画体现了一种文化特性,有文化内涵。当然不是说别的老师的画没有文化含义,而是说庞先生最接近我个人心中“ 中国文化” 的含义。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今天有幸在常熟— — 庞先生的故乡来谈这个问题。
很多人对于中国画有这样的观点:中国画太单调,中国画本身对人的刺激强度不够,中国画的外在内容太多,有段时间我也是这个看法。1995年从法国回来后,我感觉中国画强力不够,放在一个环境里面,感到它很弱。在大英博物馆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线很细,没有震撼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其实看画需要一个氛围。在一个空间里可能会感到某些画较弱,但古人的画很多是藏在袖子里拿出来共同欣赏的,距离都在一米左右,在这个空间里欣赏是最适合的,如果它放到一个庙堂里面自然就显得弱了。有的画内容是人物和山水,高四米,气势就很强,所以看画需要制造一个氛围,就像喝茶一样,喝大碗茶,那是解渴,喝完就完了,但你要品茶的时候,最好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细细地一点一点地品,功夫茶是要一点一点地品味,和解渴没有关系,它偏重于审美。我想为什么要像喝大碗茶那样去看中国画?为什么要放在一个不应该放的环境里面?能不能制造一个氛围,品读中国画的氛围?我提出我的看法,我觉得绘画更是一个文化形态,强调刺激感、现实性、时间性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画画不像时装那样,过了这个季就没用了,变成垃圾给扔掉,绘画应该研究最内在的核心,能够永恒的核心。我有一个体会,中国画最强调文化形态,在世界上也是唯一以文化综合为标准的绘画。欧洲的绘画不强调文化形态,中国画有“ 诗、文、书、印” 好多内容,有人说那些没用,是外在的,但是我认为如果运用得很好,会变成非常好的内容。比如像郑板桥、潘天寿,他们在文字和绘画的结合关系上运用的非常好,体现出人的品格。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决定,画的价值与画得“ 像不像” 没有关系,这就是文化心理。有意思的是,中国绘画在五代以前基本没有分行的,没有文人和工匠的区别,是以人物画为主的时代。西洋画派没有专门的划分,在18世纪末才出现了风景画或印象派等等。中国人有一种文化心态,因为中国强调文化,文人是主体,当官的都是文人,不像西方的画家是雇佣的工匠,绘画内容是宗教性的,为宣传宗教服务,用宗教来维持现在和警示未来的意思。但是中国画恰恰相反,尤其是中国山水画是远离这一切的,甚至是鄙视现实的心态。严格说起来应该在二到三世纪左右形成,建安时期国家很乱,出现了曹操这样的人物,人们生活很悲苦,思考人生去向问题,所以当时人的心态包括那时的艺术形式是对人生的感叹。曹操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的《长叹歌》里都是哀歌,歌颂死亡,中国人偏向这种歌曲。后来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她的哥哥长孙无忌就是以唱悲歌而闻名,他唱的是送葬歌。那时候的人对人生产生了很多感叹,由此出现两种形态:一种是特别入世的,像曹操这种人,罢黜百家,自己来做一些对人民有用的事情;另一种是闭世的状态,就是一百多年后东晋时候最盛行的,他们感觉到自己无力便躲开这些矛盾。当道教和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人们就找到一种媒介躲开社会矛盾。但是躲开社会矛盾得有条件,就像鲁迅讲的,陶渊明也是要吃饭。因为躲开社会,人物画被慢慢淡化,中国山水画出现了。当时出现很多歌颂自然的诗,不是针对人,是针对自然。这种形式由于文人的推动慢慢变成为主流,在五到六世纪,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文人,叫刘勰,他写过一本书《文心雕龙》,强调文章的写法、文字的形式、文字的分类、修辞的方式,最强调的是思路问题,就是作文中要有一个思想内容。不到几十年,就出现了谢赫的《六法论》,当时还没有山水画,《六法论》主要是针对人物画的。中国文化品位就像道教一样,像老子的观点,有一个很大的涵度,慢慢就演化为中国画的品类,成为所有形式的一个标准,就是现在讲的“ 六法” ,用气韵生动来表现山水,实际上当时最早是评判人物画的。从那时起,中国的文人就慢慢登上了中国绘画的舞台,慢慢地由山水文化走向山水艺术。但真正提倡文人思想的人,实际是四世纪的苏东坡,一千年以前他主动提出了文人画的要求:“ 我看画就像看天下的马一样,我看过了一千匹马就明白了马的好坏,然后我翻阅工匠的画,我一看就倦,但是我看文人画的时候,我就来精神了。” 他看到有思想的画的时候就来精神了,说明一个问题:绘画要有思想。以前的工匠大部分是被雇佣的,是按照客户要求来画的,没有权利和思想。文人不靠绘画吃饭,不在乎这个,就产生了自由的想法。同时又有个问题,就是技术的问题,比如郭熙,他是北宋的宫廷画家,没有多少文化,但他的绘画本事却很大,画得非常好,在临死以前由他儿子整理完成了《林泉高致集》。苏东坡多次在诗文里谈到郭熙,说他画得如何好,如何有文气,这好像和他的原意相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苏东坡是重视技术和思想的,首先重视思想,然后重视技术。山水画成为中国绘画主流是到南宋时期,他代表中国的一种思想,中国人慢慢离开了现实,走向了自然。画山水画的人基本都是文人,工匠很少,中国艺术还有个特征就是民族和民间的问题,这是一个矛盾。民间是民族的一部分,但是中国画的主流尤其在近700年,山水占主体,通过很微弱的信息,表达文人对自然的留恋,对现实的逃避,元代最明显。当然有很多画家兼有两方面,比如元代初期赵孟頫,应该说他是最保守的,也是最先进的,既有宫廷画家的功力,又有文人的情思。画画的时候和写书法相联系,这是文人的优势,赵孟頫第一次把绘画和书法放在同一个位置上。在他之前,一幅画的题字都是很小的,甚至不题字。从赵孟頫开始,经常会把绘画和书法放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赵孟頫的理论又是讲古法的,他说:“ 我的书法不看宋人也不看唐人,是看晋人,我的画法是看唐人。”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我们研究下来,唐代以前的书法折笔用得很少,气韵比较连贯;宋代、唐代以后的书法,折笔用得较多,横划很细,竖划特别粗,不是圆笔法,比较强调工艺性,晋代书法就不是这样。赵孟頫书法上学晋人,但实际创作行为上不是这样。所以有时候看一个艺术家,不要看艺术表面的东西,画得很旧,实际上旧的里面蕴藏很多新的生机。比如现代欧洲写实画家佛洛依德,他有时候突然回归到古典方法,但他的作品还是表现出新意,证明不在于表面的形式,而在于思想方式,这个就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道理。在欧洲的绘画历史上一般强调“ 像与不像” ,明暗关系“ 准与不准” ,特别强调真实性,这个理论来源是达芬奇的“ 镜子说” ,说看到这个对象就像看到镜子一样。而中国人不是这个观点,中国人认为“ 镜子观点” 是空洞的,中国传统绘画中从来没有强调这种所谓的真实。中国画像浮雕,像虚光的照片,本身不强调立体,虽然也注意到了光线和影子却从来不画倒影,这种讲法不完全对。顾恺之讲:“ 山有影,景物皆倒置。” 他的画没看到,但有文字记载,他绝对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也注意到了色彩。为什么归结到最后中国画会成为这种形态?我觉得中国画正是依靠你的这种视觉经验来完成你对绘画的理解。比如画一个月亮,勾一下线,并没有画出月亮的颜色,照你的经验理解为月亮,一看就是个月亮,靠你的识别经验启发你去识别,欣赏者和作者共同完成识别关系。它不是淋漓尽致的,淋漓尽致是栩栩如生的概念。它是用你的文化背景来理解它,完成这个审美过程,如果不够的话,就加以诗句来帮助你理解,不懂中国诗歌、不懂中国诗情的人是很难理解中国画的,这是修养问题。所以国外很多人说,看你们中国人画画用一些墨水涂来涂去,他不理解,就像我们不理解欧洲人的现代绘画,拿着一个桶泼洒颜色,泼到什么效果就是什么效果,那不是胡乱画嘛!这是文化的差异,我们没有这个文化背景。中国人需不需要理解西方人的文化背景·需不需要服从西方人的文化背景?这是个问题。
上午看了破山寺的寺院,我特别感动,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园林建筑了,真是很美。中国人非常理解,其实外国人也非常理解,这种差异性体现得非常明确,就是一种文化新意,就是一种文化审美。我们去过欧洲,去过西班牙、法国,看他们的园林简直像蛋糕一样,一片一片的,树修得像皮球一样圆,每个季节修一次。在我们看来实在太傻,其实树本来就很美,他们的愿望是把它们归一、整齐,把树弄成圆球形,在中国人看来这简直是暴敛天物,完全把它的灵性给弄没了,这就是文化差异。但是我认为不要缩小这种差异,应该保持自己的审美。北京城九个城门如果都保留下来的话,那简直太伟大了,因为建设问题给破坏了,永远不可能恢复了,这是很难受的。有时候审美就表现在文化差异上,你没有权利去强迫西方人理解你,你也没有必要按照西方人的方式来对待中国的艺术和中国人的文化形态,应该保持自己优美的东西,保持自己品功夫茶的那种感觉,而不是只为了解渴。这么说起来好像中国绘画没有现实主义似的,实际上还是有的,是体现在文化形态和浪漫心态上。中国古代很多诗歌就是这么表现的,那时可以用诗歌来汇报工作,汇报工作都能是艺术性的,多么可贵!那些奏折的文采都非常好,帝王一看就能理解,用词都很雅很讲究,绝不会出现粗暴的词句。这种文化应该保留下来,但现在都做不到,都按照公文的形式来做。
再讲中国画的“ 综合” 问题。诗、书、画、印是中国画的特征,还要看你怎么运用。也有一些运用不好的例子,比如说《富春山居图》,当时乾隆皇帝看到这幅画很激动,他的审美有限,但其实是一幅假画。他特别喜欢表现,把画带在身边,一有空就题上一首诗、题上一篇文章,一共题了53次,画面给题满了,完全没有空间了,把那画卷变成书卷了。后来发现了真迹,一看当然比假的画得好多了,但皇帝不能有错,他就在真迹上再题几首诗,最后压一个章,意思是比我题过的那个差一点。皇帝题字是显示权利,他往往不管画面的情况,甚至弄个大印盖在中间— — “ 御览之宝” ,有时像个大饼一样的糊在上面,很丑。画家就很少这样做,很少把自己很好的画面题字搞坏,除非他不是一个文化人,画家都题得很适当,因为他有审美能力。如果有点文采的话,题首诗在上面,加强对画面意境的理解,变得更完整、更美,这种结合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形式。郑板桥的画,他的石头是勾法,没有皴法,但能感觉到很厚重,这是最了不起的地方。“ 薄” 与“ 厚” 是艺术表现的两种形态,有时候他在大石头上写上一大片的字来填补空间,切割空间关系,使画面丰富有层次,把字当做画面的一部分,他是有艺术修养的人,结合得非常好,使不完美的东西变得很完美。潘天寿也是这样,他有时候故意找长线来题字,一根线拉得很长,再找另外一根线,求共性,叫“ 同形反复” ,搞摄影的都知道,一个形放大或缩小,反复出现时会产生统一。潘天寿甚至把一个东西故意强化成一个形,使画面的内容统一起来,有时感觉画面单薄,要加一条线的时候,他故意漏掉几个字,再加上一行小字补充这个空间,煞费苦心,很了不起。我看塞尚的画,塞尚早期的画很笨,很傻,后期他干脆歪打正着,反正画不准,就在画面上切割结构、研究形式,结果造就了一代大师,成为“ 立体派” 的开山之祖。人在长期磨练之后会突然产生一种自然的感觉,塞尚就是这样,他老画对面的山,天天在画,把山画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再切割面的关系,画得非常有意思。他不知道自己多伟大,当时莫奈拉着他去见罗丹,他的腿都软了,差点给罗丹跪下,他不知道自己比罗丹还要伟大。画能体现一个人的性格和人格,比如咱们看潘天寿的画,你能感觉他和你有距离,他是很孤傲的一个人,他的画也和你有距离,他的画体现那种高傲、“ 不可亵玩” ,体现他本身的性格。同样,像李苦禅先生,和他只差一岁,关系也很好,互相也有影响,但苦禅老人的画里面有一种朴实,是内在的醇厚的情感,和潘天寿完全不一样。虽然表面看他们的画很像,画的内容也差不多,但是能找到他们心里的那种差异。能找到和别人的差异,在绘画中这点很重要。我们学画时,往往会说我们像谁像谁,但到了一定时候,要做到我不像谁,一定不能像谁,要找到自己,找到真实的自己,找不到真实的自己,往往会走向歧路。和潘天寿同时期的画家张书旗,他原来是画大写意的,吴昌硕那路,画得像极了,后来他觉得不是那回事,最后他用色纸画和平鸽,最有名的作品是中国政府献给罗斯福的《百鸽图》,用色纸和白粉画的一百多只和平鸽,这就是真正的张书旗,他找到真实的自己,就有价值了。王个移的画学得特别像吴昌硕,看得一点意思也没有,这很悲剧。王雪涛先生也是这样,学齐白石学得像极了,齐白石说:有人能学到我的心,但没有人能学到我的手,只有雪涛能学到我的手,和我的一模一样,我自己都分不出来。但是最后王雪涛还是转向了,转向他自己,慢慢地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在北方他的小写意价格一路上升,已经达到几十万了,接近齐白石水平,他的价值被认同了。假如还跟着齐白石走,那他就没有任何价值,也不可能有价值。所以说要善于找到自己,根据自己的文化,根据自己的体验来找到自己。
再谈一下关于“ 印” 的问题。中国印的历史很长,从战国开始就有玺印,盖图章叫落款,阳为款(鼓起来的字叫款),阴为识(凹进去的字叫识)。发展到战国变成官员行使权利的象征,就是官印。文人用印的时间,严格说来是从赵孟頫开始的,赵孟頫自己并不刻印,他的印都是自己写好后找工匠刻的,有水晶的,有象牙的,那时还没有石印。真正刻印是从明代开始,赵孟頫作为中国第一个把书法放到绘画位置上的人,他很看重图章,他的图章都是自己设计的。当时的印泥不是油印,而是水印。咱们有时候看古画的时候,临假画的人会把现代印泥盖上去,盖在宋画上,我们一看就乐了,明显是假的,那时候根本没有印泥。像《五牛图》,我临过,知道上面有四十多个图章,就是水印,这是一个常识。印泥是到了明代慢慢调制成的,文人介入以后,产生各种流派,包括咱们常熟的“ 虞山派” 篆刻家赵古泥。印章是以耐看、浑厚、协调为目的的一种形式,是表现画面文化心态的一种重要形式。咱们还有很多传统,比如印泥有各种颜色,写挽联时盖蓝色印泥,现在很多人都盖红图章,过去是不允许这样的。有很多形式咱们可以利用和发展,包括图章。图章内容很多,有自己的志向,有自己的名号,对画面起到调节作用。毛泽东的书法从来不盖图章,别人给他刻了,他也不盖。作为画家来讲,我觉得图章是很重要,有一个女书法家提出:书法家也要写诗。虽然看她诗写得很差,还不如抄古人的诗,但是懂一些诗还是好的,对画的理解有好处,所以画面还是要注意文气。
再谈谈“ 中西” 问题。我认为中国画讲究文心,并不排除西洋画的文化气息,但是我反对一个观点,说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人在文化上绝对不可以这样的。比如说吃面包的人,怎么来理解喝豆汁的?生活地理环境和视觉习惯不能强同,也不可能强同。绘画属于视觉范畴,必然有最基本的视觉内容,如果没有视觉内容就失去了本身的价值。像现在有人搞音乐,到台上演奏的时候,一个人站着,一句话不说,过了二十分钟走了,说完成了,他就是老子的观点:大音希声— — 你自己怎么想象,你自己理解去吧。这就太虚无主义了,是离开了艺术形式所要求的基本内容。既然属于视觉艺术,就应该有视觉艺术的基本内容,同时要注意它所限定的视觉范畴的规律。民间绘画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有的很强烈,很亮,很有冲击力。所以有很多西方人看到中国的民间艺术非常激动,包括京剧,尽管听不懂,但具有典型特征,五颜六色的人在舞台上晃来晃去,很有意思。民间的艺术保留着自觉的原始的东西,这东西应该吸收。实际上,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很多好东西被文人所吸收了,比如敦煌莫高窟第220窟,我觉得画得太好了,一查时间,比阎立本的《帝王图》还要早;还有《维摩诘图》,比吴道子还要早,还要好。在古代也有个互动关系,不要蔑视传统的东西,有些被认为是最通俗的,其实在最通俗的事情当中也可以找到一些很有趣的表现内容。像明末清初的陈老莲,他把很多装饰性的元素运用到画上去,当时苏州地区的画家吴斌就是专门用装饰形式来表现平面构成关系,他吸收了很多中国民间的东西,中国民间大有可取的内容。我们看到吴冠中先生的画中用很多品色,像紫罗兰、桃红,一看很刺激,细细一品,真好,用色真好,非常强烈。他画面的内在内容并不缺乏,加上色彩,更强化了,非常有现代视觉感。文化是多元的,吸收可以从民间、民俗,可以从东方、西方,但是中心内容应该保持,应该保持中国的文化心理。
再谈一谈我个人的绘画。朋友们刚才看到我的展览,其中有很多造像,有很多人问我是什么原因画这些的?我说我并不是佛教徒,并不信仰宗教,只信仰“ 美” ,我觉得造型本身是一种无言的表达方式。比如我们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会感觉她在注意你,《蒙娜丽莎》为什么会成为经典?是你看她的时候,有多种涵盖因素在里面,你看她笑,其实没在笑,但细看好像又在笑,他的“ 度” 把握得特别好。我在中国传统造像里面看到这个元素,尤其是北魏造像,你用什么心情看她的时候,你都能得到一种回应,和你有一种互动关系。他的“ 度” 把握得很好,绝不会出现过于悲和过于喜的状态。很多搞雕塑的人临摹这些东西就是临不出那种感觉,要么过了,要么不够,程度非常难把握。这就说明,传统一旦过去以后,你想恢复它,没有那种心态是恢复不来的。就绘画来讲,每个画家都想向前推进,我认为,在推进的时候应该多加强对文化的理解,不要做表面文章,你要通过你自己找到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恰不恰当,需要时间来考验。只有通过写生才能找到那种生命的活力和真切的感受,如果你反复重复一个题目会感到很贫乏,你必须要从自然中找到一种新的生命力。像吴冠中先生,六七十岁了还去写生,非常了不起;张仃先生八十多岁的时候,我还陪着他去写生,他是从自然当中吸取一种真切的感觉。张仃先生已经过世了,在他去世前的十年,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他不画画了?因为他离开了对环境的真实感受,就不愿意来造这些东西了。他不虚伪,他必须从自然中吸取,不然他宁可不画,他的画里有一种内在的气质。有人说张仃先生的画有气而无韵,但我感觉这气本身就来自于韵。他那种情绪不是婉约的,绝对是北方人那种强悍的情绪。大家应该多从自然文化中吸取内容,找到自己的语言。中国文人往往强化修养,很多人都说只要字写得好,画就画得好,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常熟最有名的书法家翁同龢,字写得好极了,非常有厚度,很了不得的“ 庙堂字” ,按理说他的画也应该画得很好,但是我看过他的画,差极,不知道怎么会画得那么差,就是说,书法和绘画是两回事,造型是造型的问题,笔墨和造型没有直接的关系。他没有像潘天寿和齐白石那样,将两者融合得那么完美,造型感是需要用很大的功夫来训练的。
我的总体观点就是:文化本身就是中国绘画艺术的一个内容。文化是立体的,包括多种内容,历史、哲学、书法、音乐各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本身对绘画是有帮助的,大家不要忽略了画外的修养。当然更重要的是画的内容,你有很强的造型能力,才能把自己的愿望表达出来,然后加强素养,加强文化。我从庞先生的画中就体会到这点,这就是我对中国画的总体认识。
主持人:
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王老师提问。
提问者1:
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您怎样处理写生和创作的关系?要不要采用照相机来作为辅助工具?
王玉良:
写生和创作的关系,有时候是这样的,我家人说我,怎么画了那么多的写生都不用到创作中去,不都白费了吗?我感觉它们有矛盾关系,写生为什么重要?不写生就没有一种体验,就像日记一样,你记的日子忘不了,没记的日子好像不存在了,只有画过以后才有一种体验。拍照片也是一种写生手段,但写生和照片完全是两回事,拍照片过后慢慢就淡化了,但写生会好一点。我画过莫高窟,记得1989年举行一个展览时,我翻阅过去的东西,翻到十年前的速写,想到莫高窟夜晚的月亮,就根据写生的感觉把它提炼出来。莫高窟其实挺高的,还有水塔什么,高低起伏,但我当时的感觉它是沙漠,平常如水,所以我画成平。当时我画了个黑月亮,有人写了文章说什么心态?实际上只是视觉形象,以视觉经验来理解这个东西,人家误以为是月亮。写生和创作是相辅相成的,有时候用得上,有时候用不上,经过写生后体会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写生也有缺点,写生有个概括的过程,有一次我在重庆画桥、木阁楼,一开始我坐在那里,画了整整一天,一个个房子画过去,结果画完以后看,却不是那么回事,我画得那么真实,怎么就出不来效果?第二天我干脆坐在那先画线,画完线往里填内容,感觉就不一样了。写生是概括的,就像我们去西藏,看到上面雪山,下面菜花、森林,多好看啊!可是下车去找却找不着,不是找不到,而是有距离,在形式中重叠了,写生时需要组合关系。
提问者2:
王老师我想问一下,中国画侧重于文学性,西方绘画注重求真写实。现代中国画家比如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驰名中外。中国画在以后会向一个什么方向发展?会不会保持一种静态的趋势?
王玉良:
绘画从近代来讲,像林风眠、徐悲鸿等都走向西方,并从中吸收了很多好东西。去西方的人很多,但是成功者并不是太多,像林风眠是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个画家,因为和他自己的文化心理结合得比较好。有的画家把西方的东西搬过来显得比较生硬。西方绘画很有哲理,现在这种东西差异慢慢被世界所共同认识。举个例子,意大利有个画家叫莫兰迪,西方人称他为“ 洋八大” ,他把一个内容反复画,把内容扩展成无限的思想。他画瓶瓶罐罐,把它们看成是活的生命,看成各种组合方式、各种构成方式,他只是画瓶瓶罐罐,什么方法都用过,在他的瓶瓶罐罐中,整个西方美术史全部包括了。这个画家是很自闭的一个人,一生没有结婚,老在一个小城不出去。在同一个内容中,在反复描写对象中,他发现了不同的表现方式和不同的思想内容。莫兰迪在西方被推崇得很高,大家都认识到他的文化价值,实际上他的思想核心和东方的“ 八大” 有联系。“ 八大” 画荷叶,通过荷叶表现各种形式和组合方式,表现各种不同的思想情感。徐悲鸿、林风眠等等,他们有不同的社会经历,表现的内容是不同的。徐悲鸿有很强的写实性,他曾经骂过很多西方现代画家,他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国人当时还没有一个人能达到徐悲鸿的写实能力,我翻阅画册,徐悲鸿的素描人体画得实在太好了,比起西方大师一点都不逊色。他只活了58岁,画出那么多画来,很惊人。他中西结合得很好,他的书法写得那么天然,就单从书法方面,在当代画家中也只有齐白石可以和他相比,那种个性,那种醇厚,那种美感,值得肯定。徐悲鸿本身有点偏执,但是当时中国历史需要这么一个人,如果没有徐悲鸿,还会有别的人出现。历史就是这样,总有人要踏上那一步,后人才能跟上去。而林风眠没走那条路,他走的是近代艺术的路,细细看他的画,你就可以体会到他画的中国味道,一个画西画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画中国画的。就像最近抽象画家朱德群的展览,一看就是中国人画的,那种感觉和西方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他也套用西方那种形式,但核心是中国画。就像一个南方人和一个北方人,纵然这个南方人长得很粗犷,北方人长得很秀气,但在具体处事上,一看就知道他们的差异。至于刘海粟,只能算一个教育家,本身的艺术不是很成熟,他都在别人的范畴里面做,没有自己个人的格局,包括书法。林风眠则是打通了很多关系,一个是打通了中西的关系,再一个是打通了民间和文人的关系。他的画文化性强,面很宽,不是局限于绘画本身,文化修养是成就一位大师的重要方面。可能跟他接触的教育和老师有关,他所接触的内容很宽泛,所以他开创了这么一条路。这条路后来发展了很多人,像赵无极、吴冠中先生都是这个系统的。这个文化系统实际上是对中国绘画推进最大的一个系统,包括李可染。你细看李可染《爱晚亭》的逆光效果,一般人觉得李可染绘画像黄宾虹、齐白石,我感觉林风眠的成份最多,无论从视觉形式和审美感觉。李可染画的那种压抑的感觉、有挣扎的感觉、带着苦涩的感觉,和林风眠完全是一致的,他的画里很压抑,没有太多的欢乐,不是山花烂漫,骨子里的审美和林风眠在一起。比如说黄宾虹到了晚年,完全是返老还童了,他的画是山花烂漫的,还有齐白石,非常有生命力,是那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但在林风眠、李可染的画里没有这种感觉。
关于动态还是静态,刚才那位同学说“ 西方是动态的,中国是静态的” ,这个不一定,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西方的动态有时是不节制的,特别疯狂,有些近代的西方油画家,包括毕加索的画都有这种内容,带有疯狂的、下意识的。中国画也有下意识,但是有约制感,不能说“ 中国人是静态的” ,其实是一种文化约制。中国画的走笔,讲究“ 有没有来处” ,像陆俨少的一笔下去,感觉线的走笔是连笔的,接笔的时候捻一下,收锋,这个线非常耐看。像李可染画的牛,一看就知道,没有几年功夫根本就画不出这道线来,像刀切一样入木三分,他的收笔是捻的,这是个用笔技巧问题,是和书法的结合问题。中国近代的四个大画家,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都属于“ 金石派画家” 。所谓“ 金石派” ,就是他们和篆刻、书法结合最密切,笔法非常耐看,单独看都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当然,这取决于中国人,写过书法的人一看用笔,就知道他写过什么,学过什么碑,写过“ 二王” 、“ 文徵明” 等等。中国画是讲究这个的,黄宾虹走笔时那种盘旋的感觉,那种悲欢离合都能体验到,这就是绘画在“ 像” 以外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