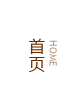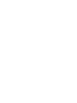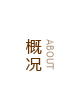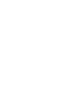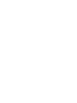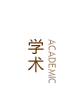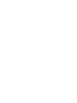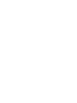一种都会感性:1927—1936年的庞薰琹艺术与中国美术现代性
2011-11-26 08:25:00来源:庞薰琹美术馆点击:7717
作 者:韩雪岩(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 博士)
出 版 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11月第1版《探索·探索·再探索— — 纪念庞薰琹先生诞辰105周年艺术展作品集》
那是,首先是,常常前去大都会,
因为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才诞生了这个挥不去的理想。
— — 波德莱尔:《致阿尔塞纳•乌塞》
(To Arsène Houssaye)
1932年傅雷(1908— 1966)在《艺术旬刊》中这样描述薰琹先生的都会气质:“ 簇新的建筑,妖艳的魔女,杂色的人种,咖啡店,舞女,沙龙,jazz音乐会,cinéma,poule,俊俏的侍女,可厌的女房东,大学生,劳工,地道车,烟突,铁塔,Montparnasse,Halle,市政厅,塞纳河畔的旧书铺,烟斗,啤酒,Porto,Comaedia,一切新的,旧的,丑的,美的,看的,听的,古文化的遗迹,新文明的气焰,自普恩加拉(Poincaré)至Joséphiné Baker,都在他脑中旋风似的打转,打转。他,黑丝绒的上衣,帽子斜在半边,双手藏在裤袋里,一天到晚的,迷迷糊糊,在这世界最大的漩涡中梦着……” 。[1]倪贻德(1901— 1970)先生在《决澜社的一群》中也回忆说:“ 当他初回国来的时候,还保持着这种巴黎艺术家的气派:黑丝绒的外衣,帽子斜在半边,双手插在裤袋内,长而蓬乱的头发,口上老是衔着烟斗……” [2]这些朋友笔下的薰琹先生都洋溢着与乡土中国明显迥异的都会感性。这种艺术家格调带来的都会感性气息与法国的浪漫主义有着密切的渊源,具有唯美的表征,同时也呈现出鲜明的“ 颓废” (la décadent)情调。
按照哈佛大学李欧梵(1942— )博士的阐释,美学意义上的“ 颓废” 乃是现代性及“ 启蒙” 思潮的另一面相[3],在民国文艺中具有特殊的意涵和社会影响。而按照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1934— )的研究,“ 颓废” 有着明晰的历史延宕脉络和审美意涵,自文艺复兴以来“ 进步和颓废的概念是如此紧密地互相包含,以至于如果我们想做出概括,就会得到一个悖论式的结论:进步即颓废,反之,颓废即进步。” [4]这种观念起源于“ 时间进程成为线性的和不可逆的— — 和对末日的信仰” [5],在思潮中则伴随浪漫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成为了“ 美学现代性” 的标志。
美学意义的“ 颓废” 就其本质而言“ 是现代性的,它允诺无限发展、民主和共同分享文明的好处” 。这一思潮有意识地培养出一种“ 自我间离的风格” ,以此来对抗“ 资产阶级自以为是的人性论和矫饰主义。” 而其萌生的基础无疑是以都会文化的兴起为背景的。因此,薰琹先生的巴黎都会风格就不仅仅是留学生涯生活习惯的延宕,同时还与回国后的都会体验有着密切的关联,更与其艺术经历、理念和创作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从而使薰琹先生“ 中国前卫艺术之父” 的称号具有了更深邃的可供挖掘的学术潜能与意涵。
一、双城记:从巴黎到上海的艺术体验
薰琹先生对浪漫主义思潮唯美理念的接受无疑是从艺术都会巴黎开始的。这种“ 美” 的陶染首先来源于巴黎日常生活中浓郁的文化氛围。他多次流连在画廊、展览会与博物馆,巴黎最活跃的文艺观念、艺术传统与创新浪潮都是随手可及的学养,如他回忆:“ 有时,我去卢佛尔博物馆,坐在维纳斯像前,一坐一两个小时,面对这样的雕像,我的心像被微风吹拂的湖面,清澈、安静。可是,当我走进另一些画廊,我的心,就像着了火。” [6]薰琹先生在进入朱利安画院(Academie Julian)学习绘画的同时,还对音乐、诗歌和舞蹈充满兴趣。其中观看玛丽•魏格孟的舞蹈记忆尤其深刻:“ 她开始起舞了,好像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大地上的一切生物,又开始活动起来。鼓声也逐渐急促起来,舞蹈的动作,从抒情的表现,转入到‘力’的表现。” [7]薰琹先生还进一步将这些视觉记忆同艺术的抽象性和纯粹性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舞蹈的主题“ 黑暗到黎明” 以及这种极具节奏与韵律感的艺术形式,对薰琹先生接受“ 颓废中的审美” 、“ 刹那中的永久” 等全新的艺术观念可谓极具启迪意义。“ 作为一种艺术观” 和“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的唯美主义思潮对年轻时期的薰琹先生的影响可谓是全方位的。
1926年与常玉(1900— 1966)的结识则对薰琹先生早期艺术观念和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常玉在巴黎的生活极具波西米亚式的艺术家风格,其绘画在东方情调与现代趣味之间寻觅出一条抒写内心情愫的独特路径。邵洵美(1906— 1968)的《巴黎的春天》与徐志摩(1897— 1931)的《巴黎的鳞爪》都描述了唯美颓废的常玉艺术与生活情境。而常玉追求纯情纯美的审美趣味以及高蹈的人格都给予了薰琹先生以启迪意义。他们常结伴去格朗•歇米欧尔学院(Académie de la Grande Chaumiére)画素描,薰琹先生还接受了常玉的建议改用毛笔来画速写,用线条的手法来进行油画创作。《藤椅上的人体》就与常玉风格有明显的关联。常玉的画面元素是东方而现代的,主旨却是追求内心澎湃激情的传达,“ 说是东方人的根性,不如说他全部是受了巴黎拉丁区的影响” ,邵洵美对他艺术的评价,同样也适用于这一阶段的薰琹艺术,因为两者都根植于一种全新的都市感性与现代体验。巴黎蒙巴纳斯(Montparnasse)的生活是浪漫的,“ La Rotonde” 、“ Le Dô;me” 和“ La Coupole” 咖啡馆作为文化艺术的中心,使艺术家们愈加体验到叛经离道,丢弃中产阶级正经的矫饰的西装革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需要和自由的情趣。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 1973)、于特里约(Utrillo Maurice,1883— 1955)、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 1876-1957)、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 1954)、波拉克(Braque,1882-1963)等巴黎画派著名的艺术家频繁地在此交流最新的艺术观念,创造出最摩登的属于艺术家的生活方式,这都使在此流连达两年之久的薰琹先生深获启发。如他自己评价:“ 在蒙巴尔纳斯的两年活动,所学到的东西,是任何学校中学不到的。” 此阶段,薰琹先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理念:“ 真。画家应该是真实地说心上所想说的话,真实地表现心上所想表现的理想与情感。……但是,也应该绝对的自然,不该追求一种方法或形式来表现,也不该太被物质的‘真’的观念所牵制。” [8]这是一种超越具象的追求情感真实的创作观,其中凝聚着唯美主义“ 为艺术而艺术” 和追求单纯的“ 象牙之塔” 的诉求。
薰琹先生的上海生活也同样充满浪漫主义的唯美气息,“ 他在上海的画室,就是蒙巴纳斯在中国的小缩影。年轻的艺术家们,聚集在他的周围,因为对他们而言,那儿应该就是巴黎了。” [9]他住在法租界里,后者构成了巴黎作为西方都会文化代表的一种“ 仿像” ,其生活方式也是巴黎式的,按照陈抱一的回忆,“ 在吕班路角上的庞薰琹画室中,他曾邀请过一次‘艺人会’。他亲自制备了多量的葡萄酒的混合酒,和各色丰美的Sandwich便餐;在他那个画室中,畅聚了一晚。在座的洋画家大概有十多人,最后共同画了一幅纪念的墨笔略画。这一种有趣的艺术联欢会,大有一点巴黎的Bohemain风趣。” [10]在“ 东方的巴黎” 中继续一种巴黎都会风格的生活方式,薰琹先生的创作理念与艺术思路自然延宕着巴黎留学期间酝酿的唯美主义审美观,表现于艺术创作则具有明显的“ 颓废” 情调。
二、都会面孔与图像隐喻
颓废概念在西方近现代文化中是一个相当明确的艺术概念,不能单纯而肤浅地理解为纵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杂糅。巴黎现代艺术的颓废风格与进步思潮可谓19世纪末期西方现代性的硬币两面。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1852-1935)是第一位将颓废作为特殊风格的成熟哲学和美学理论加以论述的社会学家。在《当代心理学论文集》中,布尔热高度强调了颓废风格与个人主义的一致性,是一种摈除了统一、等级、客观性等传统专制要求的现代性胜利。[11]卡林内斯库则强调“ 颓废的审美主义更加自觉于它的批判-论战功能,而较少把自己当成现代生活令人痛苦的不确定性和矛盾的解救之道” 。[12]因此,19世纪末期的颓废主义总是向公开提倡革命观念演变。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亦将颓废与乌托邦联系起来,沉醉于关于社会未来的思考之中。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也强调以颓废为表象的现代性不仅暗含着线性的进化观,“ 从现代到未来” 的前卫姿态才是本质。[13]
从这一角度出发,才能理解《决澜社宣言》慷慨激昂的澎湃情感与薰琹先生此阶段作品忧郁气质的矛盾性及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薰琹先生曾指出:“ 今日中国艺术精神之颓废,与中国文化之日趋堕落,辄深自痛心,但自知识浅单力薄,倾一己之力,不足以稍挽颓风,乃思集合数同志,互相研究,以力求自我之进步,集数人之力或能有所贡献于世人,此组织‘决澜社’之原由也” 。[14]则这种前卫与先锋色彩正与《如此巴黎》、《人生的哑谜》(又名《如此上海》)、《时代的女儿》、《慰》、《无题》等早期代表作互为表里。
《如此巴黎》与《如此上海》都采用了立体主义的创作手法并加以衍变,在内容上则将繁华而疯狂的夜巴黎浓缩在画面上,卖笑的女人、赤裸的身体、愁苦的眼神、叼雪茄的男人、隐现的警察、摇曳的灯光、炫目的广告,众多现代生活中的“ 摩登” 元素一并构成了奇异华丽的颓废面貌,其情绪既是苦闷而矛盾的,同时又是对现代都会生活方式的一种视觉记录与魅惑式指责。《时代的女儿》虽然抹去了都会生活的各种符号,人物的面部特征亦高度的概括化,但同样呈现出鲜明的都市韵味。她们的眉眼神情是沉郁、压抑、迷惘的,仿佛在互相倾诉冲破束缚的渴望和对自由的向往,这种直指时代弊端的浓烈情绪与《决澜社宣言》那种飞扬的音调构成了同一母题。1934年创作的《无题》在图像的隐喻性格更为突出,薰琹先生自述:“ 画面上主要画得是压榨机的剖面” 。“ 前面一个机器人,另一个是我国农村妇女像,其一是象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达,其二是象征落后的中国农业,左上方三个巨大的手指在推动压榨机,象征着帝国主义、反动的政治与封建势力,这是对我国人民进行压榨的三种势力,也就是迫得我走投无路的三种势力。” [15]湖面背景中的天使舞蹈场面则代表了薰琹先生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是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歌颂未来的希望与进步。这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带来的人性异化与压迫的深刻反思。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薰琹先生这一阶段的大量封面设计与广告设计。尽管是出于商业的实用用途,但薰琹先生笔下的人物身子无不带有都会生活的特有气息,《啤酒广告》表现了开怀畅饮者的忘乎所以,夸张的体态洋溢着浪漫的情调,而《夏洛特传》则用类似卓别林的面孔来表现,人物的神情介于滑稽与庄重之间,礼帽与领结的西式城市符号与钢丝般的鬓发构成了一种关于现代生活的调侃。
按照卡林内斯库的阐述:“ 在19世纪前半期的某个阶段,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 [16]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概念执着于“ 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只能够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 — 所有这些都以各种不同程度联系着迈向现代的斗争。” [17]这种现代性渗透于文化,呈现出一种物质主义式的中产阶级媚俗文化。而美学的现代性却是通过艺术对资产阶级趣味表达批判态度,“ 是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 ,主张艺术家通过惊世骇俗的多种方式来表达憎恶和对传统的激烈反叛,甚至采用一种自我放逐的姿态,疏离于中产阶级的物质化社会之外,在象牙塔里寻找真、善、美。艺术前卫之父是浪漫主义的旗手波德莱尔。他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对美学现代性的本质及自律性进行了廓清。在他那里,艺术家反抗异化、大众流行文化和工具理性。因此,薰琹先生的这些创作无疑属于美学前卫的范畴,是对现代生活都会文化腐朽、平庸、保守与丑陋的针砭,是自身都会生活体验与情感的传递。
需要注意的是,1933年,薰琹先生还参加了朱维基(1904— 1971)、林徽因(1904— 1955)、邵洵美等组织的“ 绿社” 。这一个唯美色彩仅次于“ 狮吼” 和“ 金屋” 社团的小团体,其重要功绩就在于通过《绿》、《声色》、《诗篇》等刊物对西方唯美、颓废主义文学进行介绍。这一社团的文学创作均流露出唯美颓唐的审美倾向,而薰琹先生自述曾在此阶段创作了二三十首诗篇,由此亦可见,他对由都会生活而来的唯美主义颓废思潮本质的洞悉与热衷。
三、中国美术现代性的滥觞
1863年波德莱尔在《费加罗报》(Figaro)上发表了评价贡斯当丹•居伊(Constantin Guys,1805-1892)的文章《现代生活的画家》,在这片文章中他塑造了关于现代画家的标准像。在第四章《现代性》中,波德莱尔声称:“ 不停地穿越巨大的人性荒漠的孤独者,有一个比纯粹的漫游者的目的更高些的目的,有一个与一时的短暂的愉快不同的更普遍的目的。他寻找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 [18]波德莱尔对现代性艺术家的评价由此分为两个层面:(1)画家能够以画笔记录“ 时代精神” ;(2)画家笔下“ 瞬间性的” 、“ 短暂的” 现代生活图景,比“ 风俗” 的含义更具体、深刻,更具时空感。因此,薰琹先生对都会感性的生动记录,就不仅意味着先锋和革命,也不仅是以唯美的笔法来对抗旧社会的禁欲和对人性的摧残,同时还是以颓废的喻像来反对中国传统的个性压抑和对个人主义的打击,是时代镜像的真实记录和情感表征。
对薰琹先生而言,这种对都会镜像的描绘不是力图对外在的客体表象进行记录,而是对由感性生活引起的情感和内在心绪进行表现。如其云:“ 艺术(Art)就是艺术家自我(Self)的表现,是人类发泄情感的工具。” “ 自我表现(Self-expression)是把自己内部的生活向外部表现之。” 而这种艺术观呈现为具体的风格则超越了现实主义与写实技法,从而走向了现代艺术趣味,是“ 与内心情感相一致的艺术‘变形’” 。如傅雷所评介:“ 他变形,因为要使‘形’有特种表白,这是Deformisme Expressive,他要给事物以某种风格(Styliser),因为他的特种心境需要特种典型来具体化。” [19]
薰琹先生的早期艺术无疑有着西方现代艺术风格的影子。然而由内在情感的自然生发,从而超越具体的造型语言,进而传递复杂的情绪与感受使其风格又形成了鲜明的个人特征。1931年所作的《拉手风琴的水手》即使最佳的明证之一。薰琹先生运用团块的手法传递出画面的整体力度,通过众多男性光头水手整齐划一的排列,形成类似兵马俑似的静止体重复,同时归纳明暗对比,赋予画作强烈光线感的,又使之进一步柔和化,使极度欢畅热烈的场景转化为东方式的抒情唯美意味,也使水手这一近代都会所包蕴的海洋文明格调平添了沉静内敛的气质。
按照邦尼•麦克多卡(Bonnie McDougall,1941— )关于中国美术现代性的观点: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为牢固的传统的社会责任感的重负所束缚,另一方面也积极投身到当时的社会活动中,因此无法真正地放弃传统,彻底革命— — 换句话说,他们太社会化,太政治角色化,缺乏艺术独立的思想和实践,而这恰恰是西方社会中美术现代性最主要的特点。[20]麦克多卡的结论显得比较偏颇。虽然中国的美术现代性缺乏西方美术现代性那样缜密的延宕谱系,但在薰琹先生的早期艺术创作中已经孕育了美术现代性的萌芽与样态,美学前卫并没有让位于政治前卫。李欧梵先生在谈及民国文艺的现代性时曾强调:“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当时各种美学现代主义在欧洲达到了巅峰,但在中国很显然没有出现此类美学上的敌对或否定态度,也没有确定的资产阶级阵营可以攻击……换言之,现代性可以成为一种文学时尚,一种理想,但它不是一种可确证的‘客观现实’。当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在急于跟上西方的同时,他们没有条件籍后视来采取一个对现代性完全敌意的姿态。” [21]这同样是可以商榷的观点。如果说薰琹先生的多年都会生活体验仅仅停留于日常浮华,则很明显与其作品的深刻意涵相去甚远,从更根本上讲,薰琹先生亦非将西方现代艺术视为可以全盘接受的偶像,以自身的文化传统吸纳涵化,自出机杼创造属于中国的现代艺术才是其意图所在,如薰琹先生强调:“ 我们不妨尽量接受外来的影响,凭他们在我们的神经上起一种融合的作用,再滤过我们的个性来著作,来创造。”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由都会文明而来的浪漫主义唯美颓废思潮内在的偏颇,包括薰琹先生在内的艺术家并未完全洞悉。尼采(Friedrich W.Nietzsche,1849-1900)曾揭示出的颓废派的内在矛盾:(一)“ 颓废的策略是典型的说谎者策略,说谎者通过模仿真理,通过使他的谎言较真理更为可信来进行欺骗。因此,在它对生活的憎恨中,颓废为装成一种较高层次生活的崇丰者……颓废是危险的,因为总是将自己伪装成与它相反的东西。” [22](二)现代性的时间意识与基督教的时间概念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其进步色彩最终会导致虚无主义。这种惊人的预见无法在承袭中国传统文化的民国土壤中开出花朵,因此,薰琹先生早期艺术呈现出的美术现代性化刺痛的力度为沉郁的忧伤和反思,归根结底是西方美术现代性与中国艺术内在文脉相洽融合的结果,也正因为这一点,使其具有了属于自身的独特表征与风格系统。
结语
1937年以后,日益动荡的时局和战争威胁,需要艺术家为现实环境承担更多的责任。大部分艺术家从社会责任感出发,选择的文艺工具和象征符号随之变换。“ 艺术的革命” 逐渐让位于“ 革命的艺术” ,中国艺坛的主流视角从“ 都会中国” 转向“ 乡土中国” ,上海作为中国都会文明的标志随着沦陷成为荒城和孤岛,都会感性赖以存在的基础渐告灭亡。薰琹先生的艺术道路亦转向迂回。由现代艺术的探索转向传统装饰纹样的梳理与工艺美术教育,中国美术现代性的早期探索并没有随着薰琹先生的艺术路径继续向前衍进。然而薰琹先生的艺术理念与创作思想却已潜伏成流,为20世纪80年代美术现代性探索的重新开启塑造了路标。恰如雨果((Victor Hugo,1802— 1885)的诗篇《播种季节的晚上》:
在深耕细作的田里升起
他高大而又黑黑的身影。
我感到他对时光的迁徙
能带来丰收,心理很肯定。
他走来走去,向远处播种,
他在广漠的平原上举步,
手在一张一张,反复无穷。
黄昏拉开它的重重夜幕,
黑暗和着夜籁,分不太清,
似把播种者庄严的手势
越传越远,一直传给星星。
参考文献:
[1][19]傅雷:《薰琹的梦》,载《艺术旬刊》第1卷第3期,1932年。
[2]倪贻德:《20世纪西画文献:倪贻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第160页。
[3](美)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4] [5](美)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 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66页、第163页。
[6]庞薰琹:《庞薰琹文选:论艺术 设计 美育》,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
[7][8]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12页。
[9](英)苏立文:《回忆庞薰琹》,《庞薰琹画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
[10]郎绍君 水天中主编:《20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
[11]Paul Bourget. Essais de psychologie contemporaine. Paris:Lemerre,1893.P.28.
[12](美)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 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87页。
[13]Jurgen Habermas, “ Modernity - An Incomplete Project” , Hal Foster, ed. The Anti - 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Seattle: Bay Press, 1983, p.9.
[14]庞薰琹:《决澜社小史》,《艺术旬刊》第1卷第5期,1932年。
[15]庞薰琹:《庞薰琹》,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16][17][22](美)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 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7-48页,第180页。
[18](法)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郭宏图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20]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Modern China, Tokyo: Centre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1971, p. 196-213.
[21](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53页。
出 版 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11月第1版《探索·探索·再探索— — 纪念庞薰琹先生诞辰105周年艺术展作品集》
那是,首先是,常常前去大都会,
因为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才诞生了这个挥不去的理想。
— — 波德莱尔:《致阿尔塞纳•乌塞》
(To Arsène Houssaye)
1932年傅雷(1908— 1966)在《艺术旬刊》中这样描述薰琹先生的都会气质:“ 簇新的建筑,妖艳的魔女,杂色的人种,咖啡店,舞女,沙龙,jazz音乐会,cinéma,poule,俊俏的侍女,可厌的女房东,大学生,劳工,地道车,烟突,铁塔,Montparnasse,Halle,市政厅,塞纳河畔的旧书铺,烟斗,啤酒,Porto,Comaedia,一切新的,旧的,丑的,美的,看的,听的,古文化的遗迹,新文明的气焰,自普恩加拉(Poincaré)至Joséphiné Baker,都在他脑中旋风似的打转,打转。他,黑丝绒的上衣,帽子斜在半边,双手藏在裤袋里,一天到晚的,迷迷糊糊,在这世界最大的漩涡中梦着……” 。[1]倪贻德(1901— 1970)先生在《决澜社的一群》中也回忆说:“ 当他初回国来的时候,还保持着这种巴黎艺术家的气派:黑丝绒的外衣,帽子斜在半边,双手插在裤袋内,长而蓬乱的头发,口上老是衔着烟斗……” [2]这些朋友笔下的薰琹先生都洋溢着与乡土中国明显迥异的都会感性。这种艺术家格调带来的都会感性气息与法国的浪漫主义有着密切的渊源,具有唯美的表征,同时也呈现出鲜明的“ 颓废” (la décadent)情调。
按照哈佛大学李欧梵(1942— )博士的阐释,美学意义上的“ 颓废” 乃是现代性及“ 启蒙” 思潮的另一面相[3],在民国文艺中具有特殊的意涵和社会影响。而按照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1934— )的研究,“ 颓废” 有着明晰的历史延宕脉络和审美意涵,自文艺复兴以来“ 进步和颓废的概念是如此紧密地互相包含,以至于如果我们想做出概括,就会得到一个悖论式的结论:进步即颓废,反之,颓废即进步。” [4]这种观念起源于“ 时间进程成为线性的和不可逆的— — 和对末日的信仰” [5],在思潮中则伴随浪漫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成为了“ 美学现代性” 的标志。
美学意义的“ 颓废” 就其本质而言“ 是现代性的,它允诺无限发展、民主和共同分享文明的好处” 。这一思潮有意识地培养出一种“ 自我间离的风格” ,以此来对抗“ 资产阶级自以为是的人性论和矫饰主义。” 而其萌生的基础无疑是以都会文化的兴起为背景的。因此,薰琹先生的巴黎都会风格就不仅仅是留学生涯生活习惯的延宕,同时还与回国后的都会体验有着密切的关联,更与其艺术经历、理念和创作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从而使薰琹先生“ 中国前卫艺术之父” 的称号具有了更深邃的可供挖掘的学术潜能与意涵。
一、双城记:从巴黎到上海的艺术体验
薰琹先生对浪漫主义思潮唯美理念的接受无疑是从艺术都会巴黎开始的。这种“ 美” 的陶染首先来源于巴黎日常生活中浓郁的文化氛围。他多次流连在画廊、展览会与博物馆,巴黎最活跃的文艺观念、艺术传统与创新浪潮都是随手可及的学养,如他回忆:“ 有时,我去卢佛尔博物馆,坐在维纳斯像前,一坐一两个小时,面对这样的雕像,我的心像被微风吹拂的湖面,清澈、安静。可是,当我走进另一些画廊,我的心,就像着了火。” [6]薰琹先生在进入朱利安画院(Academie Julian)学习绘画的同时,还对音乐、诗歌和舞蹈充满兴趣。其中观看玛丽•魏格孟的舞蹈记忆尤其深刻:“ 她开始起舞了,好像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大地上的一切生物,又开始活动起来。鼓声也逐渐急促起来,舞蹈的动作,从抒情的表现,转入到‘力’的表现。” [7]薰琹先生还进一步将这些视觉记忆同艺术的抽象性和纯粹性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舞蹈的主题“ 黑暗到黎明” 以及这种极具节奏与韵律感的艺术形式,对薰琹先生接受“ 颓废中的审美” 、“ 刹那中的永久” 等全新的艺术观念可谓极具启迪意义。“ 作为一种艺术观” 和“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的唯美主义思潮对年轻时期的薰琹先生的影响可谓是全方位的。
1926年与常玉(1900— 1966)的结识则对薰琹先生早期艺术观念和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常玉在巴黎的生活极具波西米亚式的艺术家风格,其绘画在东方情调与现代趣味之间寻觅出一条抒写内心情愫的独特路径。邵洵美(1906— 1968)的《巴黎的春天》与徐志摩(1897— 1931)的《巴黎的鳞爪》都描述了唯美颓废的常玉艺术与生活情境。而常玉追求纯情纯美的审美趣味以及高蹈的人格都给予了薰琹先生以启迪意义。他们常结伴去格朗•歇米欧尔学院(Académie de la Grande Chaumiére)画素描,薰琹先生还接受了常玉的建议改用毛笔来画速写,用线条的手法来进行油画创作。《藤椅上的人体》就与常玉风格有明显的关联。常玉的画面元素是东方而现代的,主旨却是追求内心澎湃激情的传达,“ 说是东方人的根性,不如说他全部是受了巴黎拉丁区的影响” ,邵洵美对他艺术的评价,同样也适用于这一阶段的薰琹艺术,因为两者都根植于一种全新的都市感性与现代体验。巴黎蒙巴纳斯(Montparnasse)的生活是浪漫的,“ La Rotonde” 、“ Le Dô;me” 和“ La Coupole” 咖啡馆作为文化艺术的中心,使艺术家们愈加体验到叛经离道,丢弃中产阶级正经的矫饰的西装革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需要和自由的情趣。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 1973)、于特里约(Utrillo Maurice,1883— 1955)、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 1876-1957)、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 1954)、波拉克(Braque,1882-1963)等巴黎画派著名的艺术家频繁地在此交流最新的艺术观念,创造出最摩登的属于艺术家的生活方式,这都使在此流连达两年之久的薰琹先生深获启发。如他自己评价:“ 在蒙巴尔纳斯的两年活动,所学到的东西,是任何学校中学不到的。” 此阶段,薰琹先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理念:“ 真。画家应该是真实地说心上所想说的话,真实地表现心上所想表现的理想与情感。……但是,也应该绝对的自然,不该追求一种方法或形式来表现,也不该太被物质的‘真’的观念所牵制。” [8]这是一种超越具象的追求情感真实的创作观,其中凝聚着唯美主义“ 为艺术而艺术” 和追求单纯的“ 象牙之塔” 的诉求。
薰琹先生的上海生活也同样充满浪漫主义的唯美气息,“ 他在上海的画室,就是蒙巴纳斯在中国的小缩影。年轻的艺术家们,聚集在他的周围,因为对他们而言,那儿应该就是巴黎了。” [9]他住在法租界里,后者构成了巴黎作为西方都会文化代表的一种“ 仿像” ,其生活方式也是巴黎式的,按照陈抱一的回忆,“ 在吕班路角上的庞薰琹画室中,他曾邀请过一次‘艺人会’。他亲自制备了多量的葡萄酒的混合酒,和各色丰美的Sandwich便餐;在他那个画室中,畅聚了一晚。在座的洋画家大概有十多人,最后共同画了一幅纪念的墨笔略画。这一种有趣的艺术联欢会,大有一点巴黎的Bohemain风趣。” [10]在“ 东方的巴黎” 中继续一种巴黎都会风格的生活方式,薰琹先生的创作理念与艺术思路自然延宕着巴黎留学期间酝酿的唯美主义审美观,表现于艺术创作则具有明显的“ 颓废” 情调。
二、都会面孔与图像隐喻
颓废概念在西方近现代文化中是一个相当明确的艺术概念,不能单纯而肤浅地理解为纵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杂糅。巴黎现代艺术的颓废风格与进步思潮可谓19世纪末期西方现代性的硬币两面。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1852-1935)是第一位将颓废作为特殊风格的成熟哲学和美学理论加以论述的社会学家。在《当代心理学论文集》中,布尔热高度强调了颓废风格与个人主义的一致性,是一种摈除了统一、等级、客观性等传统专制要求的现代性胜利。[11]卡林内斯库则强调“ 颓废的审美主义更加自觉于它的批判-论战功能,而较少把自己当成现代生活令人痛苦的不确定性和矛盾的解救之道” 。[12]因此,19世纪末期的颓废主义总是向公开提倡革命观念演变。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亦将颓废与乌托邦联系起来,沉醉于关于社会未来的思考之中。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也强调以颓废为表象的现代性不仅暗含着线性的进化观,“ 从现代到未来” 的前卫姿态才是本质。[13]
从这一角度出发,才能理解《决澜社宣言》慷慨激昂的澎湃情感与薰琹先生此阶段作品忧郁气质的矛盾性及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薰琹先生曾指出:“ 今日中国艺术精神之颓废,与中国文化之日趋堕落,辄深自痛心,但自知识浅单力薄,倾一己之力,不足以稍挽颓风,乃思集合数同志,互相研究,以力求自我之进步,集数人之力或能有所贡献于世人,此组织‘决澜社’之原由也” 。[14]则这种前卫与先锋色彩正与《如此巴黎》、《人生的哑谜》(又名《如此上海》)、《时代的女儿》、《慰》、《无题》等早期代表作互为表里。
《如此巴黎》与《如此上海》都采用了立体主义的创作手法并加以衍变,在内容上则将繁华而疯狂的夜巴黎浓缩在画面上,卖笑的女人、赤裸的身体、愁苦的眼神、叼雪茄的男人、隐现的警察、摇曳的灯光、炫目的广告,众多现代生活中的“ 摩登” 元素一并构成了奇异华丽的颓废面貌,其情绪既是苦闷而矛盾的,同时又是对现代都会生活方式的一种视觉记录与魅惑式指责。《时代的女儿》虽然抹去了都会生活的各种符号,人物的面部特征亦高度的概括化,但同样呈现出鲜明的都市韵味。她们的眉眼神情是沉郁、压抑、迷惘的,仿佛在互相倾诉冲破束缚的渴望和对自由的向往,这种直指时代弊端的浓烈情绪与《决澜社宣言》那种飞扬的音调构成了同一母题。1934年创作的《无题》在图像的隐喻性格更为突出,薰琹先生自述:“ 画面上主要画得是压榨机的剖面” 。“ 前面一个机器人,另一个是我国农村妇女像,其一是象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达,其二是象征落后的中国农业,左上方三个巨大的手指在推动压榨机,象征着帝国主义、反动的政治与封建势力,这是对我国人民进行压榨的三种势力,也就是迫得我走投无路的三种势力。” [15]湖面背景中的天使舞蹈场面则代表了薰琹先生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是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歌颂未来的希望与进步。这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带来的人性异化与压迫的深刻反思。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薰琹先生这一阶段的大量封面设计与广告设计。尽管是出于商业的实用用途,但薰琹先生笔下的人物身子无不带有都会生活的特有气息,《啤酒广告》表现了开怀畅饮者的忘乎所以,夸张的体态洋溢着浪漫的情调,而《夏洛特传》则用类似卓别林的面孔来表现,人物的神情介于滑稽与庄重之间,礼帽与领结的西式城市符号与钢丝般的鬓发构成了一种关于现代生活的调侃。
按照卡林内斯库的阐述:“ 在19世纪前半期的某个阶段,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 [16]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概念执着于“ 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只能够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 — 所有这些都以各种不同程度联系着迈向现代的斗争。” [17]这种现代性渗透于文化,呈现出一种物质主义式的中产阶级媚俗文化。而美学的现代性却是通过艺术对资产阶级趣味表达批判态度,“ 是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 ,主张艺术家通过惊世骇俗的多种方式来表达憎恶和对传统的激烈反叛,甚至采用一种自我放逐的姿态,疏离于中产阶级的物质化社会之外,在象牙塔里寻找真、善、美。艺术前卫之父是浪漫主义的旗手波德莱尔。他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对美学现代性的本质及自律性进行了廓清。在他那里,艺术家反抗异化、大众流行文化和工具理性。因此,薰琹先生的这些创作无疑属于美学前卫的范畴,是对现代生活都会文化腐朽、平庸、保守与丑陋的针砭,是自身都会生活体验与情感的传递。
需要注意的是,1933年,薰琹先生还参加了朱维基(1904— 1971)、林徽因(1904— 1955)、邵洵美等组织的“ 绿社” 。这一个唯美色彩仅次于“ 狮吼” 和“ 金屋” 社团的小团体,其重要功绩就在于通过《绿》、《声色》、《诗篇》等刊物对西方唯美、颓废主义文学进行介绍。这一社团的文学创作均流露出唯美颓唐的审美倾向,而薰琹先生自述曾在此阶段创作了二三十首诗篇,由此亦可见,他对由都会生活而来的唯美主义颓废思潮本质的洞悉与热衷。
三、中国美术现代性的滥觞
1863年波德莱尔在《费加罗报》(Figaro)上发表了评价贡斯当丹•居伊(Constantin Guys,1805-1892)的文章《现代生活的画家》,在这片文章中他塑造了关于现代画家的标准像。在第四章《现代性》中,波德莱尔声称:“ 不停地穿越巨大的人性荒漠的孤独者,有一个比纯粹的漫游者的目的更高些的目的,有一个与一时的短暂的愉快不同的更普遍的目的。他寻找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 [18]波德莱尔对现代性艺术家的评价由此分为两个层面:(1)画家能够以画笔记录“ 时代精神” ;(2)画家笔下“ 瞬间性的” 、“ 短暂的” 现代生活图景,比“ 风俗” 的含义更具体、深刻,更具时空感。因此,薰琹先生对都会感性的生动记录,就不仅意味着先锋和革命,也不仅是以唯美的笔法来对抗旧社会的禁欲和对人性的摧残,同时还是以颓废的喻像来反对中国传统的个性压抑和对个人主义的打击,是时代镜像的真实记录和情感表征。
对薰琹先生而言,这种对都会镜像的描绘不是力图对外在的客体表象进行记录,而是对由感性生活引起的情感和内在心绪进行表现。如其云:“ 艺术(Art)就是艺术家自我(Self)的表现,是人类发泄情感的工具。” “ 自我表现(Self-expression)是把自己内部的生活向外部表现之。” 而这种艺术观呈现为具体的风格则超越了现实主义与写实技法,从而走向了现代艺术趣味,是“ 与内心情感相一致的艺术‘变形’” 。如傅雷所评介:“ 他变形,因为要使‘形’有特种表白,这是Deformisme Expressive,他要给事物以某种风格(Styliser),因为他的特种心境需要特种典型来具体化。” [19]
薰琹先生的早期艺术无疑有着西方现代艺术风格的影子。然而由内在情感的自然生发,从而超越具体的造型语言,进而传递复杂的情绪与感受使其风格又形成了鲜明的个人特征。1931年所作的《拉手风琴的水手》即使最佳的明证之一。薰琹先生运用团块的手法传递出画面的整体力度,通过众多男性光头水手整齐划一的排列,形成类似兵马俑似的静止体重复,同时归纳明暗对比,赋予画作强烈光线感的,又使之进一步柔和化,使极度欢畅热烈的场景转化为东方式的抒情唯美意味,也使水手这一近代都会所包蕴的海洋文明格调平添了沉静内敛的气质。
按照邦尼•麦克多卡(Bonnie McDougall,1941— )关于中国美术现代性的观点: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为牢固的传统的社会责任感的重负所束缚,另一方面也积极投身到当时的社会活动中,因此无法真正地放弃传统,彻底革命— — 换句话说,他们太社会化,太政治角色化,缺乏艺术独立的思想和实践,而这恰恰是西方社会中美术现代性最主要的特点。[20]麦克多卡的结论显得比较偏颇。虽然中国的美术现代性缺乏西方美术现代性那样缜密的延宕谱系,但在薰琹先生的早期艺术创作中已经孕育了美术现代性的萌芽与样态,美学前卫并没有让位于政治前卫。李欧梵先生在谈及民国文艺的现代性时曾强调:“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当时各种美学现代主义在欧洲达到了巅峰,但在中国很显然没有出现此类美学上的敌对或否定态度,也没有确定的资产阶级阵营可以攻击……换言之,现代性可以成为一种文学时尚,一种理想,但它不是一种可确证的‘客观现实’。当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在急于跟上西方的同时,他们没有条件籍后视来采取一个对现代性完全敌意的姿态。” [21]这同样是可以商榷的观点。如果说薰琹先生的多年都会生活体验仅仅停留于日常浮华,则很明显与其作品的深刻意涵相去甚远,从更根本上讲,薰琹先生亦非将西方现代艺术视为可以全盘接受的偶像,以自身的文化传统吸纳涵化,自出机杼创造属于中国的现代艺术才是其意图所在,如薰琹先生强调:“ 我们不妨尽量接受外来的影响,凭他们在我们的神经上起一种融合的作用,再滤过我们的个性来著作,来创造。”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由都会文明而来的浪漫主义唯美颓废思潮内在的偏颇,包括薰琹先生在内的艺术家并未完全洞悉。尼采(Friedrich W.Nietzsche,1849-1900)曾揭示出的颓废派的内在矛盾:(一)“ 颓废的策略是典型的说谎者策略,说谎者通过模仿真理,通过使他的谎言较真理更为可信来进行欺骗。因此,在它对生活的憎恨中,颓废为装成一种较高层次生活的崇丰者……颓废是危险的,因为总是将自己伪装成与它相反的东西。” [22](二)现代性的时间意识与基督教的时间概念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其进步色彩最终会导致虚无主义。这种惊人的预见无法在承袭中国传统文化的民国土壤中开出花朵,因此,薰琹先生早期艺术呈现出的美术现代性化刺痛的力度为沉郁的忧伤和反思,归根结底是西方美术现代性与中国艺术内在文脉相洽融合的结果,也正因为这一点,使其具有了属于自身的独特表征与风格系统。
结语
1937年以后,日益动荡的时局和战争威胁,需要艺术家为现实环境承担更多的责任。大部分艺术家从社会责任感出发,选择的文艺工具和象征符号随之变换。“ 艺术的革命” 逐渐让位于“ 革命的艺术” ,中国艺坛的主流视角从“ 都会中国” 转向“ 乡土中国” ,上海作为中国都会文明的标志随着沦陷成为荒城和孤岛,都会感性赖以存在的基础渐告灭亡。薰琹先生的艺术道路亦转向迂回。由现代艺术的探索转向传统装饰纹样的梳理与工艺美术教育,中国美术现代性的早期探索并没有随着薰琹先生的艺术路径继续向前衍进。然而薰琹先生的艺术理念与创作思想却已潜伏成流,为20世纪80年代美术现代性探索的重新开启塑造了路标。恰如雨果((Victor Hugo,1802— 1885)的诗篇《播种季节的晚上》:
在深耕细作的田里升起
他高大而又黑黑的身影。
我感到他对时光的迁徙
能带来丰收,心理很肯定。
他走来走去,向远处播种,
他在广漠的平原上举步,
手在一张一张,反复无穷。
黄昏拉开它的重重夜幕,
黑暗和着夜籁,分不太清,
似把播种者庄严的手势
越传越远,一直传给星星。
参考文献:
[1][19]傅雷:《薰琹的梦》,载《艺术旬刊》第1卷第3期,1932年。
[2]倪贻德:《20世纪西画文献:倪贻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第160页。
[3](美)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4] [5](美)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 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66页、第163页。
[6]庞薰琹:《庞薰琹文选:论艺术 设计 美育》,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
[7][8]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12页。
[9](英)苏立文:《回忆庞薰琹》,《庞薰琹画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
[10]郎绍君 水天中主编:《20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
[11]Paul Bourget. Essais de psychologie contemporaine. Paris:Lemerre,1893.P.28.
[12](美)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 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87页。
[13]Jurgen Habermas, “ Modernity - An Incomplete Project” , Hal Foster, ed. The Anti - 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Seattle: Bay Press, 1983, p.9.
[14]庞薰琹:《决澜社小史》,《艺术旬刊》第1卷第5期,1932年。
[15]庞薰琹:《庞薰琹》,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16][17][22](美)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 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7-48页,第180页。
[18](法)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郭宏图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20]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Modern China, Tokyo: Centre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1971, p. 196-213.
[21](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53页。